第四章 南朝文学
南朝文学的基本特点,从内容来说,主要反映文人自身的日常生活情趣和周围环境,以及他们所认识到的人生的普遍现象。有关山水自然、有关女性以及男女之情的题材,得到了集中的表现。从艺术形式来说,正如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所说:“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一转关也。”与魏晋诗人不同,南朝诗人更崇尚声色,追求艺术形式的完善与华美,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真实的性情。尤其是出现了四声,产生了诗的格律,加快了五言诗向着近体诗迈进的步伐。在文章方面,魏晋以来骈偶化的倾向进一步发展,文章变得更加工整,并在后期逐渐形成所谓“四六文”的体制。
第一节 元嘉文学
元嘉(424—454)是宋文帝刘义隆的年号,刘宋时期的主要作家大多活跃在这一阶段,代表人物有史称“元嘉三大家”的谢灵运、鲍照和颜延之。谢灵运所开创的山水诗,把自然界的美景引进诗中,使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他的创作,不仅把诗歌从“淡乎寡味”的玄理中解放了出来,而且加强了诗歌的艺术技巧和表现力,并影响了一代诗风。鲍照的乐府诗,唱出了广大寒士的心声,他在诗歌艺术上的探索与创新也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一、谢灵运与山水诗
谢灵运(385-433),小字阿客,故称谢客,自幼送入道馆,15岁时回家。出身显赫,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附近),世居会稽。祖父为谢玄,封康乐公。灵运袭祖父爵位,世称谢康乐 ,自幼才学出众,很早就受到族叔谢混的赏识,与从兄谢瞻、谢晦等皆为谢氏家庭中一时之秀。宋初刘裕采取压抑士族的政策,谢灵运也由公爵降为侯爵,食邑由三千户降到五百户。在政治上一直不得意,这自然使他心怀愤恨。《宋书》本传说他“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少帝即位,权在大臣,灵运构扇异同,非毁执政”。自出任永嘉太守之后,无论是在任还是隐居,他总是纵情山水,肆意遨游,且“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一方面以此举对抗当政,发泄不满,同时也在山水清音之中得到心灵的慰藉。由于其大规模的游山活动惊动了官府和朝廷,朝廷命他为临川(江西抚州)内史。但恣意山水之举依然遭到弹劾,朝廷派人缉捕欲以法办,谢灵运买通强人强劫囚车,终于触怒朝廷,被就地斩首。
早在《诗经》和《楚辞》的时代,诗中就出现了山水景物,但那往往只是作为生活的衬景或比兴的媒介,而不是作为一种独立的审美对象。其后,曹操的《观沧海》、左思的《招隐诗》和郭璞的《游仙诗》都写到山水美景,在客观上为后来的山水诗提供了艺术经验。魏晋以来,士大夫阶层大都以山林为乐土,他们往往把自己理想的生活和山水之美结合起来,因此山水描写的成分在诗里就逐渐多了起来。
晋宋时代,江南的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士族地主阶层的物质生活条件更加优越,他们大造别墅,在秀美的山水之间过着登临吟啸的悠闲生活。而作为生活环境的山水景物,也就很自然地反映在诗中。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
山水诗的产生,与当时盛行的玄学和玄言诗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的玄学把儒家提倡的“名教”与老庄提倡的“自然”结合在一起,引导士大夫从山水中寻求人生的哲理与趣味。真正的玄言家,是很懂得 之理的。因此在玄学发展的过程中,山水审美的意识也渐增。借山水体玄,成为当时一种普遍的风气。在玄言诗里,也常常寓玄理于山水之中,或借山水以抒情,因而出现了不少描写自然山水的佳句,可以说玄言诗本身就孕育了山水诗。
晋宋之际,随着自然山水审美意识的不断浓厚,山水绘画及理论也应运而生。这对于山水诗的产生,无疑也有着促进的作用。在山水诗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庾阐、殷仲文和谢混等人,都曾有过一定的贡献。但真正大力创作山水诗的,则是刘宋的谢灵运。
谢灵运的山水诗,大部分是他任永嘉太守以后所写。这些诗,以富丽精工的语言,生动细致地描绘了永嘉、会稽、彭蠡湖等地的自然景色。其主要特点是鲜丽清新,如《南史·颜延之传》载:“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此外,汤惠休说“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采镂金(装饰文采,刻镂金属)”(锺嵘《诗品》卷中引)。一方面,与颜诗的“铺锦列绣”、“雕缋满眼”相比,谢诗显得“自然”;另一方面,当人们读厌了那些 “淡乎寡味”的玄言诗,而一接触到谢诗中那些山姿水态与典丽新声时,自然会感到鲜丽清新、自然可爱。
沈德潜曾将谢诗与陶诗作过比较:“陶诗合于自然,不可及处,在真在厚。谢诗经营而反于自然,不可及处,在新在俊。”(《说诗晬语》卷上)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看,魏晋和南朝属于两个不同的阶段:魏晋诗歌上承汉诗,总的诗风是古朴的;南朝诗歌则一变魏晋的古朴,开始追求声色。而诗歌艺术的这种转变,就是从陶谢的差异开始的。陶渊明是魏晋古朴诗歌的集大成者,谢灵运却另辟蹊径,开创了南朝的一代新风。具体说来,从陶到谢,诗歌艺术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从写意到摹象。
在谢灵运之前,中国诗歌以写意为主,摹写物象只占从属的地位。陶渊明写诗不过是自然的流露,因此他无意于模山范水,只是写与景物融合为一的心境。谢灵运则不同,山姿水态在他的诗中占据了主要的地位,“极貌以写物”(《文心雕龙·明诗》)和“尚巧似”(《诗品》)成为其主要的艺术追求。他尽量捕捉山水景物的客观美,力图把它们一一真实地再现出来。
谢灵运的那些垂范后世的佳句,无不显示着高超的描摹技巧,如:
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过始宁墅》)
晓霜枫叶丹,夕曛岚气阴(《晚出西射堂》)
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登江中孤屿》)
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入彭蠡湖口》)
残红被径隧,初绿杂浅深(《读书斋》)
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
语言工整精练,境界清新自然,从不同的角度向人们展示着大自然的美。
其次是从启示性到写实性。
陶渊明的诗歌,十分注重言外的效果,发挥语言的启示性,以调动读者的联想和想象。正如他所说:“言尽意不舒”;“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诗中的物象描写,常采用白描的手法,虽然只是淡淡的几笔,但在平淡的外表下,却蕴含着炽热的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谢灵运的诗歌语言,则更注重写实性。他充分发挥了语言的表现力,增强了语言描写实景实物的效果。他凭着细致的观察和敏锐的感受,运用准确的语言,对山水景物作精心细致的刻画,力求真实地再现自然美,其笔下的物象带有独立性和客观性。
总的来说,谢诗不像陶诗那样以写意为主,注重物我合一,注重语言的启示性,而是更注重山水景物的描摹刻划,注重语言的写实性,这些山水景物又往往是独立于诗人性情之外的,因此他的诗歌也就很难达到陶诗那种情景交融、浑然一体的境界。同时在结构上,谢灵运的山水诗也多是先叙出游,次写见闻,最后谈玄或发感喟,形成了一个有些僵化的模式。如《登池上楼》: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痾对空林。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诗人久病在床,当春日来临之际禁不住开窗眺望,倾耳、举目间,浓浓的春意,盎然的生机,让诗人百感交集,不由得伤古悼今。《诗经·豳风·七月》:“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在感伤古人的同时,诗人对自身的处境也颇感不安,单居独处的生活,倍觉时光匆匆流逝;离开至爱亲朋,心情格外难以安定。当然,诗人最后还是表达了持操隐遁的心志。再看《岁暮》:
殷忧不能寐,苦此夜难颓。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运往无淹物,年逝觉已催。
诗人夜不能寐,是因为有深深的忧愁,虽然他并没有说出所忧为何。在这样一种心境之下,他来到户外,面对明月、积雪和朔风,更增加了忧伤。最后发出了时光匆匆,人生短暂的慨叹。
从陶渊明到谢灵运的诗风转变,正反映了两代诗风的嬗递。如果说陶渊明是结束了一代诗风的集大成者的话,那么谢灵运就是开启了一代新诗风的首创者。在谢灵运大力创作山水诗的过程中,为了适应表现新的题材内容和新的审美情趣,出现了“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和“性情渐隐,声色大开”的新特征。这一新的特征乃是伴随着山水诗的发展而出现的创新现象。这新的特征成为 “诗运转关”的关键因素,它深深地影响着南朝一代诗风,成为南朝诗风的主流。
颜延之也写过不少山水诗。他与谢灵运齐名,当时并称为“颜谢”。其实他的成就远不及谢灵运。锺嵘《诗品》将他列入中品,并说:
其源出于陆机。尚巧似。体裁(风格)绮密,情喻渊深。动(动笔)无虚散(空虚散漫),一句一字,皆致意(用心)焉。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虽乖(违反)秀逸,是经纶(处理)文雅才;雅才减若人,则蹈于困踬矣。
“尚巧似”是他与谢灵运诗的共同特征,然而比谢诗更加锤炼雕饰,凝练规整,且喜搬弄典故,堆砌辞藻,而缺乏情致,因此他的诗被鲍照称为“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被汤惠休称为“如错采镂金”。
二、鲍照与乐府诗
字明远,出身寒微,钟嵘说他“才秀人微,取湮当代”(《诗品》)。他是一位极有抱负的才士,不甘于自己低下的地位,迫切地想凭借自己的才智,在上层社会找到一席之地。但在豪门士族的压抑下,他有志难伸。自步入仕途后,就一直沉沦下僚,常常是在贫病交迫之中艰难度日。
他的诗歌现存200首左右,其中乐府诗有80多首。明显分成五言古体和乐府体两大类。主要成就在乐府体,这些诗用辞警醒,色泽浓郁,节奏奔放,显示出感情的冲动、激荡与紧张,极少有松弛平缓之笔。梁代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将当代文体,分为三种,其中之一是:
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魄。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
这主要指鲍照的乐府诗而言,尽管语带贬意,概括还是较为准确。
在鲍照的乐府诗中,更多的是倾泻内心的不平之愤。而且他常常把自身的体验引伸为对整个社会的认识,代表贫寒之士对贵族垄断权力、独享荣华的现状提出强烈的抗争,并在诗中反映普通民众的不幸遭遇。这使得鲍照的诗歌具有南朝其他诗人很少具有的较为广阔的社会面。五言乐府《代东武吟》以拟古的形式,写汉代一个士兵少壮从军,老暮归来,虽九死一生,立下战绩,却不得封赏,晚景凄凉困苦。《拟行路难》十八首为代表的七言乐府,主要从自身处境和感受出发,尤多感愤不平之辞,艺术上更有独创性。
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
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
二诗均写贫士失遇的苦闷,但充满抗争的精神,感情充沛而强烈。句式长短不齐,富于变化。前诗突出一个“愁”字,所叹者愁,酌酒为消愁,悲歌为泻愁,不敢言者更添愁。正如沈德潜所说,此诗“妙在不曾说破,读之自然生愁”(《古诗源》卷十一)。在平淡的外表下蕴含着深沉而又激越奔放的感情。后首前四句情绪慷慨,激愤难抑。他拔剑击柱,仰天长叹,悲愤满怀,因为有志难伸。中六句以轻松的口吻表现罢官后的天伦之乐,在轻松的背后,隐含着失志后无可奈何的悲哀。末二句故作旷达之语,既有孤寒之士的人生隐痛,也有讽刺权贵的意味。
鲍照在七言诗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以七言句为主而杂以其他各种句式的乐府歌行,是鲍照的新创。可以说他既是第一个有意识致力于七言诗创作的诗人,又是杂言式七言歌行的开创者。他所开创的这一诗型,音节错综变化,大体隔句用韵,雄恣奔放,尤其适宜表达激荡不平的感情。所以唐代李白等诗人,尤其喜好使用它进行创作。
鲍照还是南朝最早有意识地写作边塞题材的诗人。这些诗不一定反映当时实际发生的战争,从其创作意识来说,主要是通过战争、边塞风光、军旅生活等激动人心的内容,追求高度紧张、富于刺激、雄壮有力的诗情。这是鲍照的性格和审美趣味的反映。以后梁、陈的诗人普遍重视边塞题材的独特的审美价值,无疑与鲍照的影响有关。他的边塞诗虽然为数不是很多,但涉及的方面颇为广泛。如《代出自蓟北门行》,着重写将士为国捐躯的壮烈情怀。“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四句,写沙场景象,雄峻有力,渲染出悲壮的情调。而后以“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收结,就丝毫不显得空洞了。《拟行路难》之十三写远离故土的将士对家乡、妻子的怀念。如“我初辞家从军侨,荣志溢气干云宵。流浪渐冉经三龄,忽有白发素髭生。今暮临水拔已尽,明日对镜复已盈。但恐羁死为鬼客,客思寄灭生空精。每怀旧乡野,念我旧人多悲声。……”《代东武行》则写了军中的不平等。可以说,后世边塞诗所涉及的内容,在鲍照诗中大都可以见到。
鲍照乐府诗的总体艺术成就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概括:
首先,鲍照的乐府诗,抒发了贫寒之士的强烈呼声,表现为昂扬激越之情、慷慨不平之气和难以抑制的怨愤,无论写景写人,都带有鲜明的主观感情色彩,其风格俊逸豪放,影响了唐代李白、杜甫等大诗人。胡应麟《诗薮》称其“上挽曹、刘之逸步,下开李、杜之先鞭”。
其次,鲍照的乐府诗,多得益于汉魏乐府和南朝民歌的艺术经验。学习汉魏乐府的作品,多在题前冠一“代”或“拟”字;学习南朝民歌的作品,明确标出吴声、西曲的歌名,如《吴歌》三首、《采菱歌》七首等。鲍照的乐府诗把汉魏乐府的质朴刚健与南方民歌的艳丽浅俗结合起来,再加以文人创作的辞采,在语言风格上显示出新的特点。此后梁代诗人追求雅俗结合,可谓鲍照诗歌艺术的延续。
鲍照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也是一位杰出的辞赋与骈文作者。他的《芜城赋》与《登大雷岸与妹书》,都是盛传不衰的杰作。
《芜城赋》以夸张笔法将广陵城昔日的繁荣与它在宋代两次遭到兵祸后的荒凉景象相对照,哀叹战争的惨重破坏和世事迁变无常,透露了非常沉重的时代的伤感,同时也有讥刺权势者繁华如梦的意味。
《登大雷岸与妹书》,是鲍照在从建康去江州的途中,写给妹妹鲍令晖的家书。书中除首尾略述旅途之感受外,基本都是对所见自然景色的描写,运用赋体的手法,是当时文章的新体。语言风格,与作者其他诗文相类,色彩瑰丽,用辞雄健有力。
第二节 永明文学
永明(483—494)是齐武帝萧赜(ze)的年号,是萧齐文学的黄金时代。当时围绕着武帝次子竟陵王萧子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学集团。其中最著名的是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八人,号为“竟陵八友”。竟陵王子良尝夜集学士,刻烛为诗,四韵者则刻一寸,以此为率。(萧)文琰曰:“顿烧一寸烛,而成四韵诗,何难之有?”乃与(丘)令楷、江洪等共打铜钵立韵,响灭则诗成,皆可观览。沈约和周颙是声韵学的专家,他们把考辨四声的学问运用到诗歌创作中,创为四声八病之说;谢朓、王融等人也积极参与这种新体诗的创作,因为这种新体诗形成于永明年间,故又称“永明体”。《南史·陆厥传》说:
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为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二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四声是根据汉字发声的高低、长短而定的。陈寅恪先生认为,四声的提出,是由于受佛经转读的影响,除去入声以外,其余三声“实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又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也”(《四声三问》)。这种观点,今人也有反对者。不过佛经的翻译和唱诵对从汉语语音本身特点所形成的四声说,应该有一定的启示性。
音乐中按宫商角徵羽的组合变化,可以演奏出各种优秀动听的乐曲;而诗歌则可以根据字声调的组合变化,使声调按照一定的规则排列起来,以达到铿锵、和谐,富有音乐美的效果,即所谓“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沈约《宋书·谢灵运》)。具体说,以五言诗的两句为一基本单位,一句之内,平仄交错,两句之间,平仄对立。另外又要求避免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等八种声韵上的毛病。“八病”的规定过于苛细,当时人已不能完全遵守,后来定型的律诗也并不避忌所有“八病”。日本僧人空海[遍照金刚]的《文镜秘府论·西卷·文二十二种病》云:
平头诗者,五言诗第一字不得与第六字同声,第二字不得与第七字同声。……上尾诗者,五言诗中,第五字不得与第十字同声,名为上尾。
另外,句中第二字与第五字同声为“蜂腰”;第一句与第三句末字同声为“鹤膝”;一联中九字不得与末字同韵为“大韵”;句中字不得有同韵为“小韵”;一句中隔字双声为“旁纽”;一联中不得有同音字为“正纽”。
启功先生认为,南朝有四声无八病,“八病”说首先是唐人提出来的,后代遂以讹传讹,即便空海对八病的解说也不完全准确,尤其是“蜂腰”与“鹤膝”,算不上是声病(《诗文声律论稿》65-66页)。
除了四声八病的讲究,永明体还有一些写作上的习惯。如篇幅通常在十句左右,也有大量八句诗存在。除首尾二联外,中间大都用对仗句。
声律的运用首先是在五言诗的范围内。大致到陈代,五律已经基本成熟,后来唐人将之改进得更为细密并加以定型化。七言诗的律化主要是在唐代完成的。在诗歌走向律化的同时,骈文、辞赋也受到影响,出现讲究平仄、调谐声韵的现象,只是不像诗歌那样严格。由于运用声律以求新变,从总体上说,齐代以后的诗文都更加严整工丽。
在永明体产生的过程中,沈约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南史·沈约传》载沈约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然而关于“此秘未睹”之说,陆厥与沈约曾有过争论,后来锺嵘对此也有过异议,其实问题的关键即在于是否将声律的知识自觉地运用到实际创作之中。
四声的发现和永明体的产生,使诗人具有了掌握和运用声律的自觉意识,它对于增加诗歌艺术形式的美感、增强诗歌的艺术效果,是有积极意义的。
一、沈约
在永明体的诗人之中,沈约在当时甚有名望,诗歌成就也较为突出。锺嵘《诗品》以“长于清怨[清新幽怨]”概括沈约诗歌的风格。这种特征主要表现在他的离别诗之中。如《别范安成》: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
将少年时的分别同如今暮年时的分别相对比,已经蕴含了深沉浓郁的感伤之情;末二句又用战国时张敏屡次于梦中寻访好友高惠,半途迷路而回的典故(见《文选》李善注引《韩非子》),更加重了黯然离别的色彩。全诗语言浅显平易,但情感表达得真挚、深沉而又委婉。沈德潜评此诗:“一片真气流出,句句转,字字厚,去‘十九首’不远。”(《古诗源》卷十二)
《颜氏家训·文章》曾记载了沈约的“三易”说:“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所谓“易见事”,是指用典必须明白晓畅;“易识字”,是反对使用生涩偏僻的字词;“易读诵”,是指声律和谐。“三易”说的提出,是与永明文学的整体特征相一致的。
二、谢朓
谢朓字玄晖,与同族前辈谢灵运均擅长山水诗,后人有“大小谢”的并称。谢朓经常出入竟陵王萧子良的藩邸,为“八友”之一,享有很高的文学声誉。后在荆州任随王萧子隆幕僚,深受赏爱。再后来谢朓因遭受谗言逐渐陷入困境,最终被诬陷下狱而死,年仅三十六岁。因其做过宣城太守,故有谢宣城之称。
谢朓在山水诗方面的贡献,是继承了谢灵运山水诗细致、清新的特点,但又不同于谢灵运那种对山水景物作客观描摹的手法,而是通过山水景物的描写来抒发情感意趣,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地步。从而避免了大谢诗的晦涩、平板及情景割裂之弊,同时还摆脱了玄言的成分,形成一种清新流丽的风格。如《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灞涘望长安,河阳视京县。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馀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鸟覆春州,杂英满芳甸。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宴。佳期怅何许,泪下如流霰。有情知望乡,谁能鬒不变?
诗人以自然流畅的语言,将眼前层出不穷、清丽多姿的自然景观编织成一幅色彩鲜明而又和谐完美的图画,使读者感受到春天的色彩、声音和气息;而这明媚秀丽的景物又与诗人思乡的情思自然融合,显得深婉含蓄,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李白在《金陵城西楼月下吟》诗中就赞叹道:“月下沉吟久不归,古来相接眼中希。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足见其感人之深。
同谢灵运一样,谢朓也善写佳句,对仗工整,和谐流畅,清新隽永,体现了“新体诗”的特点。正如钟嵘所说:“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诗品》)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
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
朔风吹飞雨,萧条江上来(《观朝雨》)
苍翠望寒山,峥嵘瞰平陆(《冬日晚郡事隙》)
馀雪映青山,寒雾开白日(《高斋视事》)
日出众鸟散,山暝孤猿吟(《郡内高斋闲望答吕法曹》)
谢朓的一些短诗也很出色,如《玉阶怨》:“夕殿下珠帘,流萤飞复息。长夜缝罗衣,思君此何极!”又《王孙游》:“绿草蔓如丝,杂树红英发。无论君不归,君归芳已歇。”这些小诗不仅语言清新,富于南朝民歌的气息。同时它们对后来五言绝句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一定影响。
谢朓曾说“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南史·王昙首传》附《王筠传》),要达到“圆美流转”,语言的清新流畅与声韵的铿锵婉转是十分重要的因素,这与沈约所说的“三易”说是相通的。谢朓是“永明体”的积极参与者,他的诗音调流畅和谐,读起来琅琅上口,铿锵悦耳。如《游东田》:
戚戚苦无悰,携手共行乐。寻云陟累榭,随山望菌阁。远树暖阡阡,生烟纷漠漠。鱼戏新荷动,鸟散馀花落。不对芳春酒,还望青山郭。
语言清新晓畅而又富于思致,音韵铿锵而又富于变化,尤其是“戚戚”、“阡阡”、“漠漠”等双音词的运用,更增强了形象性和音韵美。流动的音声之美同诗中充满动态美的山水景色相配合,使画面更加细腻秀美、清丽自然,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而其中所蕴含的深长细微的诗思与情致,也同样使人“觉笔墨之中,笔墨之外,别有一段深情妙理”(沈德潜《古诗源》卷十二)。沈约在《伤谢朓》诗中所说:“吏部信才杰,文锋振奇响。调与金石谐,思逐风云上。”就是对谢朓诗歌这一突出特征的肯定与赞美。
谢朓是永明体的代表诗人,他不仅在当时就享有盛名,而且对后来唐诗的繁荣也有着相当深刻的影响,甚至像李白和杜甫那样的诗歌巨匠也为之倾倒。如前文所述,李白在《金陵城西楼月下吟》诗中已对谢朓作过高度的评价。此外他还说:“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我吟谢朓诗上语,朔风飒飒吹飞雨。”(《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杜甫也说:“礼加徐孺子,诗接谢宣城。”(《陪裴使君登岳阳楼》)“谢朓每篇堪讽诵,冯唐已老吹听嘘。”(《寄岑嘉州》)这些足以说明谢朓对唐代诗人的深刻影响。
另一位积极参与创制“永明体”的王融,也是颇有才华的诗人。锺嵘说他 “有盛才,词美英净”(《诗品》卷下)。《南齐书》本传也说:“融文辞辩捷,尤善仓卒属缀,有所造作,援笔可待。”王融诗歌的主要特点是构思含蓄而有韵致,写景细腻而清新自然,语言华美而平易流畅,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与谢朓相近似的风格。如他的《临高台》:
游人欲骋望,积步上高台。井莲当夏吐,窗桂逐秋开。花飞低不入,鸟散远时来。还看云栋影,含月共徘徊。
写景清新细腻,造语清新精巧,并表现出一种含婉不露的情韵。后人常把他的诗同谢朓的诗相混,可见他们的诗风确有共同之处。
第三节 梁陈文学
梁代文学延续了齐代文学的发展趋势,许多作家的活动也跨越两代,所以习惯上常以“齐梁文学”并称。但梁代文学也出现了不少新的现象,成为南朝文风最盛的一个时期。从社会环境来说,自梁朝建立至侯景之乱,武帝萧衍当政达四十七年之久,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政权稳定时间最长的时期,这为文学的繁荣提供了较好的条件。而萧衍、萧统、萧纲、萧绎父子数人,都爱好文学,并都有一定的创作成就和理论上的建树,也刺激了文学的兴盛。
陈代主要作家大都在梁代就开始了创作活动,并且与梁代几个重要的文学集团有各种关系,所以,陈代文学基本上是沿着梁代文学的道路继续发展的。由梁入陈的徐陵、阴铿、张正见、江总,和由梁流寓北朝的庾信、王褒等人,虽处于异域,而时代相同,他们共同构成了南北朝文学向唐代文学过渡的重要环节。
一、梁前期作家
1、萧衍
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与齐帝室为同宗,乘齐内乱,起兵夺取帝位。晚年因自东魏归降的大将侯景叛乱,攻破都城,他饥病而死。萧衍在齐时为“竟陵八友”之一,预西邸文士之列,不仅对文学创作有浓厚的兴趣,而且文学修养亦颇为出众。自即皇帝位后,尤能重用文士,倡导并鼓励文学创作。《梁书·文学传序》载:“高祖聪明文思,光宅区宇,旁求儒雅,诏采异人,文章之盛,焕乎俱集。每所御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善者,赐以金帛,诣阙庭而献赋颂者,或引见焉。其在位者,则沈约、江淹、任昉,并以文采,妙绝当时。”他精通音乐,爱好民歌。现存诗作九十余首,半数以上是乐府诗,而且大都模仿南朝民歌。如《子夜四时歌》十六首,与民歌可谓无所区别、维妙维肖。除了仿作,他还依照西曲制作了《襄阳蹋铜蹄》、《上云乐》、《江南弄》等新曲。其中《江南弄》七曲均以七言句与三言句组合而成,有固定的格式,故后人论词的起源,或追溯及此。其音节轻快优美,如第三曲《采莲曲》:
游戏五湖采莲归,发花田叶芳袭衣,为君艳歌世所希。世所希,有如玉,江南弄、采莲曲。(和云:采莲渚,窈窕舞佳人。)
除了乐府诗,萧衍的其他一些诗篇,也有模仿民歌风格的。以他的特殊地位而如此爱好民歌,对梁代诗风的演变,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2、何逊
曾任尚书水部郎,故称何水部。羁旅与酬答是其诗歌主要内容,两者往往又结合为一体。工于写景抒情,讲究声律,文辞清新,颇有谢朓的风致。但比起谢朓来,何逊诗在语言的锤炼上,用功更深。谢诗常常以出语天然取胜,何诗则主要以修辞的简练精当擅场(李白偏爱谢朓而杜甫偏爱何逊,也从侧面反映了何逊与谢朓的区别)。何逊诗在语言、声律及意象选择与抒情的配合诸方面都更接近唐诗的风格。如《临行与故游夜别》:
历稔共追随,一旦辞群匹。复如东注水,未有西归日。夜雨滴空阶,晓灯暗离室。相悲各罢酒,何时同促膝?
中间两联对偶,前一联用“比”的手法,后一联则以凄清的意境渲染了离情别绪。何逊的五言四句诗也有几篇佳作,其中《相送》最为著名:
客心已百念,孤游重千里。江暗雨欲来,浪白风初起。
由于篇幅较小,后二句写景中又蕴涵着很强的动势,所以就显得颇有力度。后两句可谓意在言外,暗示未来的风波险阻。
何逊年轻时受到沈约和范云的赏识。沈约曾说:“吾每读卿诗,一日三复,犹不能已。”范云也曾说:“顷观文人,质则过儒,丽则伤俗,其能含清浊、中古今,见之何生矣。”(《梁书·何逊传》)这一评价对了解何逊很重要。就是说,何逊既接受了当代文学中很多新的因素而加以发展,主要的风格又与齐梁时代逐渐盛行起来的绮艳流荡不同,能够独标一格,于浅显中见其清雅精炼。他的修辞纯熟与情景密合的特点,受到唐代诗人的高度重视。尤其是杜甫,一再说:“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能诗何水部”(《北邻》),很是倾心。
3、吴均
吴均在梁代与何逊齐名,但二人的诗歌风格并不相同。《南史·吴均传》说:“均文体清拔有古气,好事者或学之,谓之吴均体。”此所谓“清拔有古气”,主要指吴均的五言诗语言比较质朴,对仗不务工巧,而追求一种雄迈的气势。吴均的骈文成就很高,以三篇写山水风景的书信最有代表性。《与朱(宋)元思书》中,富春江的山水仿佛是活动着的生命,“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急湍猛浪,寒树高山,都有一种郁勃不平之气。《与施从事书》写故彰县的青山景色;《与顾章书》写家乡吴兴梅溪山一带的山水景色,都极富韵味。
二、萧统与《文选》
萧统乃武帝长子,立为太子而早卒,谥“昭明”,故后人习称为昭明太子。史传称其“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坟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可见他对文学的兴趣。围绕着他的太子东宫,一度形成一个兴旺的文学集团。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活动不及当时其他文学集团繁荣,成就也不高;而在学术方面的活动较多,且成就突出。尤其是《文选》三十卷的编纂,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相当深远。
《文选》又称《昭明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所录始于先秦而迄于梁,而以魏晋以后作品占据较大比重。共录130人的514篇作品,不录存者,按文体和题材分类编排。共计37种文体,赋和诗比重最大,赋按题材分为15门,诗按题材分为23门。在编选中明确注意到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所以除了诗、赋二大类,对于文章,主要选能独立成篇而又富于文采的。儒家的经书、诸子书,以及历史著作,均被排除。这种区别方法,不尽符合现代的文学概念。比如对历史著作,不收人物传记,而只收录了一部分史传的论赞,因其较讲究文采。这是当时人对文学的一种认识。但不管怎样,其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意识,还是非常重要的。
至于收录作品的标准,学界一直有争议。总的来看,《文选》明显偏向文人化的典雅华美,与当代重视雅俗结合的新风气有所不同。所以收入辞赋特别多。在诗歌部分,各时代分别最受重视的诗人是曹植、王粲、陆机、潘岳、谢灵运、颜延之诸人。民歌以及风格近俗的文人诗则选得很少。因此全书成为传统的文人文学的一次总结。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文选》毕竟汇集了历史上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不但起到保存和流布的作用,也为后代文人提供了较好的学习范本。在唐代这部书就受到高度重视,有所谓“文选学”之名。李白曾经“三拟《文选》,不如意,辄焚之”。杜甫写给儿子的《宗武生日》诗中,也叮嘱他“熟精《文选》理”。北宋前期一度有“《文选》烂,秀才半”(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的谚语。
关于《文选》的研究,早在隋代就开始了,萧该(萧统族侄)有《文选音义》。唐高宗时李善的《文选注》,引书达一千七百种,其注释偏重说明语源和典故,略于文意的疏通。今天最好的通行本就是清代胡克家翻刻南宋尤袤刻李善注本。唐玄宗时有《五臣注文选》,因学力不深,故影响不大。宋代有人将五臣注本与李善注本合刻,称“六臣注”。近人高步瀛有《文选李注义疏》,最为精博,但全书并未完成。骆鸿凯有《文选学》,是第一部通论之作。今人研究《文选》,取得了丰硕成果。郑州大学古籍所《文选研究集成》包括十二项选题,其中已有几项陆续出版。
三、梁陈宫体诗
梁武帝普通年间至陈代末年的近七十年中,以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徐摛、庾肩吾和陈后主陈叔宝等人相继提倡的宫体诗风开始兴起并逐渐占据了诗坛的统治地位,其余风所及,甚至波及到隋代和初唐的近百年间。
所谓的宫体诗,从内容上来说,主要是以宫廷生活为描写对象,将目光停留在女性的生活圈内,包括她们的容貌、体态、服饰及器物等方面,可以说,他们对女性的审美观照,同对器物的审美观照的心理是一样的。从声韵、格律上来说,比永明诗人更为精致。从风格上来说,由永明体的轻绮变为秾丽,有的作品甚至流为淫靡。
为什么宫体诗会如此兴盛?这其中自有重要的现实因素。
首先,政治、经济环境的安定,使文人习于逸乐,思想也日趋狭窄。梁武帝萧衍在位的四十多年时间,绝大部分时期维持着升平气象,梁代现存作家作品的数量也超过了其他三代的总合。
其次,文坛追求新变思想的影响。“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南齐书·文学传论》),新变本身不是坏事,但关键看如何去变。诗风一变于元嘉,二变于永明,三变于梁普通之后。由于生活和思想的贫乏,第三次追新只能停留在声韵格律和用事对偶上。
再次,南朝设有乐府机构,曾采集大量的民歌配乐演唱,以满足统治者纵情声色的需要;统治者及宫廷文人也有润色或拟作新声歌曲的习惯。南朝乐府歌辞几乎全是男女言情之作,正适合于统治者的生活情调,自然更能得到他们的青睐。这样一来,南朝民歌便从市井进入了宫廷。
最后,南朝皇室皆行伍出身,来自社会下层,入主皇宫后,在过着奢侈糜烂宫廷生活的同时,仍留恋、学习市井之风习。他们的提倡,对于宫体诗风的流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下面来看两首有代表性的诗歌,萧纲《咏内人昼眠》:
北窗聊就枕,南檐日未斜。攀钩落绮障,插捩举琵琶。梦笑开娇靥,眠鬟压落花。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红纱。夫婿恒相伴,莫误是倡家。
看来贵妇的装扮、姿态已经与倡家无异,不然何出此言?可见,在男人眼里,女人终究是被赏玩的对象。再如陈叔宝《玉树后庭花》:
丽宇芳林对高阁,新妆艳质本倾城。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
可谓轻艳至极。
对于宫体诗的评价问题。过去对于宫体诗的评价有失偏颇,主要原因在于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儒家的文学观要求诗歌成为“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工具,而对词则不作这样的要求,视为一种娱乐性的文学。宫体诗中的艳情之作,比之于唐宋词里的许多作品,从内容到风格并无二致,但对于宫体诗的批评却极少加之于词。着或许就是宫体作为诗而非词的悲哀。
总的来说,对于宫体诗的客观评价,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眼:
第一,在创作倾向上,宫体诗不值得肯定,因为在那里看不到有意义的社会生活,看不到对人生的积极追求,甚至看不到诗人个性的自我表现。
第二,在内容上,贫乏肤浅是宫体诗的致命弱点。女性不是爱情的对象而是欣赏的对象;着力描写的是女性的貌和态,而非情。
第三,在风格上,过于单一,纪昀所谓“如出一手”;此外,就是过于秾丽、浮艳以至淫靡、卑弱。
第四,在艺术形式上,宫体诗仍有其贡献。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宫体诗发展了吴歌西曲的艺术形式,并继续了永明体的艺术探索而更趋格律化。《梁书·庾肩吾传》云:“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虽是批评的口吻,但也说明宫体诗在格律化方面比沈约等人的永明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萧纲的《采菱曲》:
菱花落复含,桑女罢新蚕。(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
桂棹浮星艇,徘徊莲叶南。(仄仄平平仄,平平平仄平)
再如徐摛的《咏笔》:
本自灵山出(入),名因瑞草传。 (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
纤端奉积润,弱质散芳烟。 (平平仄平仄,仄仄仄平平)
直(入)写飞蓬牒(入),横承落絮篇。(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
一(入)逢提握重,宁忆仲升捐。 (仄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
这或许是现存最早的一首完整的五律,比庾肩吾的《岁尽应令诗》还要完整。这类诗在宫体诗中所占的比例是相当大的。这说明宫体诗对后来律诗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至于宫体诗语言的风华流丽、对仗的工稳精巧以及用典隶事等方面的艺术探索和积累,也同样为唐代诗人提供了足资借鉴的艺术经验。
四、其他陈代作家
1、徐陵
有“一代文宗”之称。年轻时与父徐摛一起出入于萧纲门下,为宫体文学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专收艳情诗的《玉台新咏》,就是由他奉萧纲之命编成的。他又与庾信并称为“徐庾”,而所谓“徐庾体”,有时被当作宫体的代名词。《陈书》本传说他:“其文颇变旧体,缉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传写成诵,遂被之华夷,家藏其本。”可见他在当时影响之大。
徐陵的诗歌留传至今的,大约只有四十篇。《杂曲》是一首七言歌行,内容系赞美陈后主之妃张丽华的美貌。形式上四句一转韵,平仄韵相间,比梁代歌行更为和谐婉转,并奠定了初唐歌行的基本格式。
徐陵同时也以文章著称。他的《玉台新咏序》,旧时很负盛名,其特点在于语言的华丽与工巧,典故用得极多,但有过于堆砌之病。
2、江总
陈代后期,围绕着后主陈叔宝,形成一个宫体文学集团。其中江总最为著名。他身居权要,而不问政事,唯与后主游宴为乐,史书责之“君臣昏乱,以至于灭”。但作为文学家,他的才华仍为后世所重。李商隐《赠牧之》云:“前身恐是梁江总。”就是拿他比拟自己的朋友杜牧。
《陈书》本传称江总“于五言、七言尤善”。史书中专门提及某人善为七言诗的,江总是第一个。从内容来说,江总的七言诗大都属于所谓艳情之作,其中有不少是传统的民歌题材。虽说无多新意,却也不应以“绮艳”二字一笔抹杀。如《闺怨篇》:
寂寂青楼大道边,纷纷白雪绮窗前。池上鸳鸯不独自,帐中苏合还空然。屏风有意障明月,灯火无情照独眠。辽西水冻春应少,蓟北鸿来路几千。愿君关山及早度,念妾桃李片时妍。
这种诗大抵以辞采的艳丽和音节的流荡取胜。内容写女子因别离而惋惜青春,是自汉代乐府和古诗以来最常见的题材。因其讲求平仄和对仗,后代也有人认为此诗已开唐人排律之体。
江总的五言诗中,也有一些佳作。尤其是陈亡以后入仕于隋时所作绝句《于长安归还扬州九月九日行薇山亭赋韵》:
心逐南云逝,形随北雁来。故乡篱下菊,今日几花开?
写思乡之情,言简意长,寄慨深沉。
3、阴铿
与何逊齐名并称,诗歌风格相似,以写景见长,但也有不同之处。如《江津送刘光禄不及》:
依然临江渚,长望倚河津。鼓声随听绝,帆势与云邻。泊处空余鸟,离亭已散人。林寒正下叶,钓晚欲收纶。如何相背远,江汉与城闉。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远去的帆影,和江边萧散的秋色,诗人送别不及,孑然一身,怅惘若失,真可说是一幅清空淡远的图画。大抵阴铿诗写景成分较何逊更多,面画感更强,而语言的雕琢痕迹较浅,有一种清灵的感觉。可惜作品传世甚少。
第四节 南朝乐府歌辞
大部分保存在郭茂倩《乐府诗集·清商曲辞》里。主要有吴歌和西曲两类。吴歌共326首,西曲共142首。《乐府诗集》卷四十四引《晋书·乐志》说:“吴歌杂曲,并出江南。东晋已来,稍有增广。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南京),吴声歌曲起于此也。”又卷四十七引《古今乐录》说:“按西曲歌出于荆(湖北省江陵县)、郢(江陵县附近)、樊(湖北省襄樊市)、邓(河南邓县)之间,而其声节送和与吴歌亦异,故依其方俗而谓之西曲云。”可见这些歌辞本来是徒歌,由乐府机构采集以后才入乐的。从时间上来说,吴歌产生于东晋及刘宋的居多,西曲于宋、齐、梁、陈的居多。清商曲辞中还有神弦歌一类,共18首,是民间祀神的乐章。清商曲辞外,在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中,也保存有少量作品。
现存南朝乐府歌辞的内容比较狭窄,绝大多数是情歌。《乐府诗集》卷六十一引《宋书·乐志》说:“自晋迁江左,下逮隋、唐,德泽浸微,风化不竞,去圣逾远,繁音日滋。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南朝和汉代一样设有乐府机构,负责采集民歌配乐演唱。汉代统治者采集民歌尚有“观风俗,知薄厚”(《汉书·艺文志》)的目的,而南朝统治者采集民歌则完全是为了满足其纵情声色的需要。
南朝乐府歌辞中多清丽缠绵的情歌,与江南幽美的自然环境和充裕的经济条件也有着直接的关系。那里山青水秀,鸟语花香。本自多情的青年男女,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免油然生发出怀春之情。长江流域物产丰盛,商业发达。而最为富庶的地区又首推荆扬二州。李延寿在《南史·循吏传》的序论中描写宋、齐盛世之时说:“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永明继运,……十许年中,百姓无犬吠之惊,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渌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南朝乐府歌辞大部分就是城市中的产物。它们多半出自商贾、妓女、船户和一般市民之口,主要反映城市中下层居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
现存的吴声歌中,以《子夜歌》(42首)、《子夜四时歌》(75首)、《华山畿》(25首)和《读曲歌》(89首)最为重要。吴声歌曲多为女性的吟唱,其内容或表现对于爱情的渴望,或表现既得爱情的欢乐,或表现相思的痛苦,或表现坚贞不渝的爱情,或表现对于负心男子的怨恨,或表现婚姻不自由的苦闷等等。这些作品,以清新浅近的语言,表现真挚细腻的感情,风格艳丽柔弱、哀怨缠绵,真实地再现了江南女子在爱情问题上的复杂心态,并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西曲产生于长江中游和汉水两岸的城市,以江陵为中心。由于地区的差别和歌者的身份不同,它多写水边船上旅客商妇的离别之情,所反映的生活面比吴歌稍广,而且更多地表现了劳动人民的爱情生活,其突出的特点是结合劳动来描写爱情。因此在情调上与吴歌的闺阁气息有所不同,风格也较为开朗明快。
南朝乐府歌辞的形式特点,体制小巧,大多为五言四句,语言清新自然。大量运用双关语。双关语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同音异字的,如:以“藕”双关“偶”,以“莲”双关“怜”,以 “丝”双关“思”,以“碑”双关“悲”,以“篱”双关“离”等;另一类是同音同字的,如:以布匹之“匹”双关匹偶之“匹”,以药名或曲名之“散”双关取散之“散”,以关门之“关”双关关念之“关”,以黄连之“苦”双关相思之 “苦”等。这些巧妙的双关语的运用,不仅使得语言更加活泼,而且在表情达意上也更加含蓄委婉。
除吴歌和西曲之外,在《杂曲歌辞》中还有一篇抒情长诗《西洲曲》。
本诗写一个青年女子的相思之情,中间穿插着不同季节的景物变化和女主人公的活动、服饰及仪容的点染描绘,一层深过一层地展示人物内心的情思,将那种无尽的相思表现得极为细腻缠绵而又委婉含蓄。全诗主要有三个情节。第一个情节是前六句,春天里的折梅寄远。“折”是实写,“寄”是虚写。第二个情节是中间十二句,秋天里的采莲怀人。“忆梅”实为忆郎,“采莲”同为忆郎。第三个情节是最后十四句,青楼上的仰望飞鸿。“西洲”不同寻常的意义,得到了凸显。
全诗以女子的动作相连缀,使人物的思想感情时刻处于动态之中;时空的频繁转换更体现了女子对爱情的执着;语气上以女子的第一人称为主,辅以第三人称的描写与咏叹;基本上是四句或两句一换韵,韵随意转,声逐情移,又运用了连珠格的修辞法,从而形成了回环婉转的旋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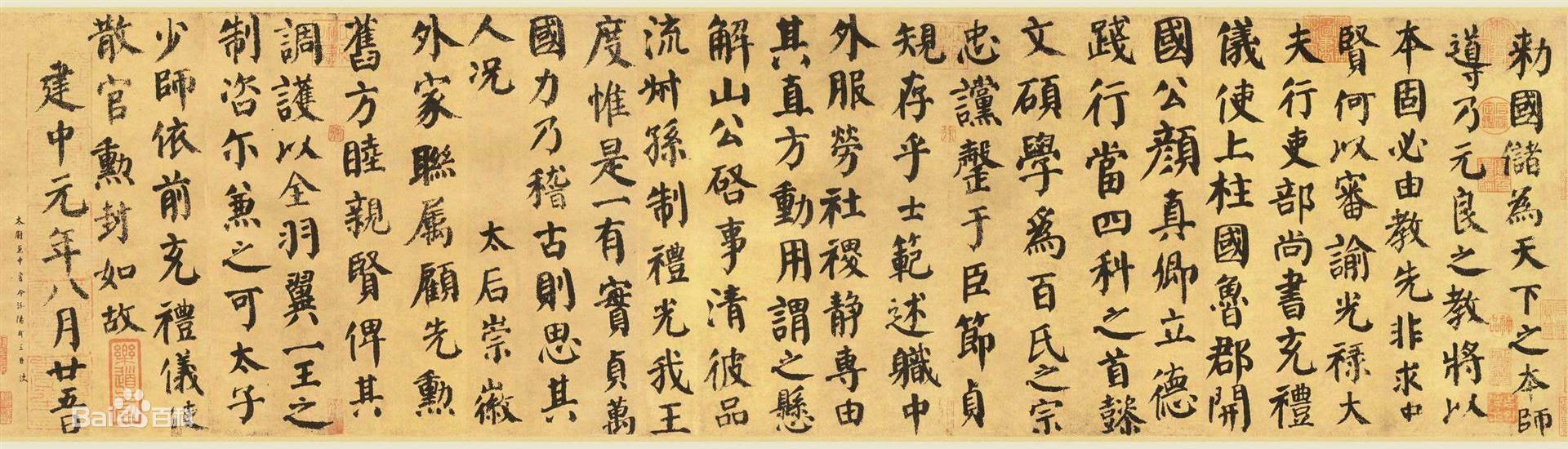
 第一章(建安文学).ppt
第一章(建安文学).ppt
 2、第二章(两晋文学).pptx
2、第二章(两晋文学).pptx
 3、第三章(陶渊明).pptx
3、第三章(陶渊明).pptx
 第四章(南朝文学).ppt
第四章(南朝文学).ppt
 第五章(北朝文学).ppt
第五章(北朝文学).ppt
 第六章(六朝小说).ppt
第六章(六朝小说).ppt
 1、绪论、第一章 隋代文学.ppt
1、绪论、第一章 隋代文学.ppt
 1、绪论、第一章 隋代文学.ppt
1、绪论、第一章 隋代文学.ppt
 3、第三章 盛唐文学.pptx
3、第三章 盛唐文学.pptx
 3、第三章 盛唐文学.ppt
3、第三章 盛唐文学.ppt
 4、第四章 李白.pptx
4、第四章 李白.pptx
 5、第五章 杜甫.pptx
5、第五章 杜甫.pptx
 6、第六章 中唐文学.pptx
6、第六章 中唐文学.pptx
 2、第二章 初唐文学.pptx
2、第二章 初唐文学.pptx
 2、第二章 初唐文学.ppt
2、第二章 初唐文学.ppt
 7、第七章 唐传奇与笔记小说.ppt
7、第七章 唐传奇与笔记小说.ppt
 8、第八章 晚唐文学.ppt
8、第八章 晚唐文学.ppt
 9、第九章 唐五代词.pptx
9、第九章 唐五代词.ppt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