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史(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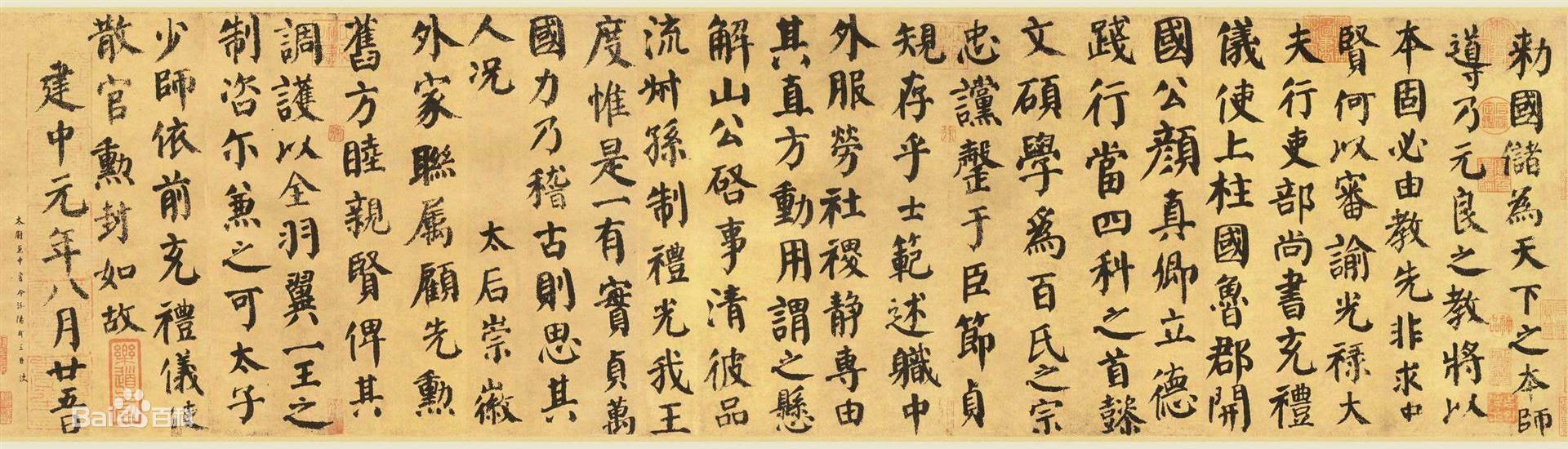
课程介绍
本课程是为本科二年级开设的专业必修课,目的在于使学生系统了解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时期文学的发展情况,掌握相关知识,培养专业意识,提升理论素养。课程内容主要是按历史时段来介绍不同时期的文学发展,对于重要的作家或文体,会以专章的方式来做细致讲授。要求学生在听课的同时,能够认真阅读、背诵相关文学作品,勤学善问。
- 2022-01-03
 第一章(建安文学).ppt
第一章(建安文学).ppt
- 2022-01-03
 2、第二章(两晋文学).pptx
2、第二章(两晋文学).pptx
- 2022-01-03
 3、第三章(陶渊明).pptx
3、第三章(陶渊明).pptx
- 2022-01-03
 第四章(南朝文学).ppt
第四章(南朝文学).ppt
- 2022-01-03
 第五章(北朝文学).ppt
第五章(北朝文学).ppt
- 2022-01-03
 第六章(六朝小说).ppt
第六章(六朝小说).ppt
- 2021-01-07
 1、绪论、第一章 隋代文学.ppt
1、绪论、第一章 隋代文学.ppt
- 2021-01-07
 1、绪论、第一章 隋代文学.ppt
1、绪论、第一章 隋代文学.ppt
- 2022-01-03
 3、第三章 盛唐文学.pptx
3、第三章 盛唐文学.pptx
- 2022-01-03
 3、第三章 盛唐文学.ppt
3、第三章 盛唐文学.ppt
- 2022-01-03
 4、第四章 李白.pptx
4、第四章 李白.pptx
- 2022-01-03
 5、第五章 杜甫.pptx
5、第五章 杜甫.pptx
- 2022-01-03
 6、第六章 中唐文学.pptx
6、第六章 中唐文学.pptx
- 2022-01-03
 2、第二章 初唐文学.pptx
2、第二章 初唐文学.pptx
- 2022-01-03
 2、第二章 初唐文学.ppt
2、第二章 初唐文学.ppt
- 2022-01-03
 7、第七章 唐传奇与笔记小说.ppt
7、第七章 唐传奇与笔记小说.ppt
- 2022-01-03
 8、第八章 晚唐文学.ppt
8、第八章 晚唐文学.ppt
- 2022-01-03
 9、第九章 唐五代词.pptx
9、第九章 唐五代词.pptx
中国古代文学史(二)
1、袁行霈、罗宗强 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版。
2、郁贤皓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2版。
3、罗宗强著:《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6年版。
4、[梁]钟嵘撰 、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5、罗宗强著:《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9年版。
6、陶敏、李一飞著:《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中华书局200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