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两晋文学
西晋政权未能建立起良好的政治秩序,就沉湎于享乐。司马炎以曹魏宗室孤弱、不能救助王室为戒,分遣同姓诸侯统率精兵镇守要地,终于导致了“八王之乱”。趁此机会,汉、魏以来大量内迁的北方少数民族的首领纷纷自立,摧毁了晋朝在北方的统治。西晋从立国到覆灭(265-317)只有大约五十年。
西晋时期,一般文学之士为了家族和个人的利益,纷纷向统治集团和当朝权贵靠拢,于是士风发生了改变。正始士人的纵诞任情,多少包含着对现实不满及拒绝与权势者合作的意味。而现今的士人既然立身于统治集团之中,就不能不有所检束,更多想到的是自身的得失,普遍流露一种自全的心态。
文学同样发生着变化。此前,无论是刚健明朗的建安文学,还是隐晦曲折的正始文学,都充溢着内在的热情,作品大多富有生气和力度。因为建安文人和正始文人是在冲突与对抗中生活的,无论是追求建功立业,还是在被压迫中痛苦挣扎,都可以说是自我意志与外部力量的抗衡。而西晋时期社会表面上是稳定的,文人自身的利益又与统治集团的利益一致,因而他们的生活就缺乏冲突与对抗,文学因而普遍显得松弛而平缓,少有激动人心的力量。换言之,文学的“风骨”在这时明显地减弱了。但是,西晋文坛并不冷落。无论作家还是作品的数量,都远远超出前代。尤其是诗歌,在士人生活中的价值进一步得到肯定,上层文士几乎没有不写诗的。
表现人生的伤感仍然是文学的中心主题,文学的抒情性,被陆机《文赋》直接揭示出来。只是由于社会的压抑,作家又缺乏对抗的意识,文学中感情往往只是表现为无奈甚至是空泛的低沉,很少有激烈、紧张、丰满的内涵。而文学作为修辞艺术的一面,受到更多的重视,建安文学追求华丽的倾向被发展到极端。使用偶句的普遍性,一首诗中偶句所占的比率,以及对偶的工整程度,都远远超过建安诗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写景的成分在西晋诗中也有明显的增加,并且写得更为细致工巧。《文心雕龙·才略》称陆机“思能入巧”;《诗品》称张协“巧构形似之言”,又称张华“巧用文字,务为妍冶”,主要都是表现在写景方面,可见这是一种普遍的风气。他们的作品缺乏壮阔的情怀,于细微处感觉却很敏锐,能准确地捕捉景物的特点并加以精细的表现,这是前人未曾达到的,对于提高诗歌的语言表现能力和审美价值有重要贡献。并且,从建安到西晋,诗歌中写景成分的增加和表现力的提高,也为山水诗的出现提供了必要的准备。
西晋文学也有几个不同的创作阶段,以太康时期为高峰。另外,这时期不同的作家作品也呈现出了各异的创作风貌。
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建康即帝位,建立了东晋王朝。此时北方五胡交战,兵连祸结,并时时觊觎江南。东晋王朝建立之初,曾数次北伐,均告失败。北方既不可恢复,江南又山清水秀,南渡士人就在此安居下来。司马睿建国,完全依赖北方南下的大士族和当地土著士族的支持,皇室的力量,远不能与西晋相比。门阀势力,更为强大,对于皇权的相对独立性,也更其明显。丞相王导曾向明帝历数司马懿父子“创业之始,诛夷名族”之事,用意即在于要求尊重士族的地位。可以说,东晋百年间的政权实际是由士族和皇室共同支撑的。
第一节 傅玄与张华
一、傅玄
字休奕。以乐府诗见长。尤其善写女性生活,《豫章行·苦相篇》:
苦相身为女,卑陋难再陈。儿男当门户,堕地自生神。雄心志四海,万里望风尘。女育无欣爱,不为家所珍。长大逃深室,藏头羞见人。垂泪适他乡,忽如雨绝云。低头和颜色,素齿结朱唇。跪拜无复数,婢妾如严宾。情合同云汉,葵藿仰阳春;心乖甚水火,百恶集其身。玉颜随年变,丈夫多好新。昔为形与影,今为胡与秦。胡秦时相见,一绝逾参辰。
他用汉乐府《豫章行》的旧题写现时情事,从女子出生、成长到嫁人以至婚后生活的整个过程中,揭示了妇女地位的低下。傅玄能将这类诗中的女子写得如此传神,得益于他对女性生活和命运的关注,这在《秋胡行》《秦女休行》等故事性乐府中也有所体现。明代张溥云:“休奕天性峻急,正色白简,台阁生风。独为诗篇,新温婉丽,善言儿女。强直之士怀情正深,赋好色者何必宋玉哉?”(殷孟伦《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准确揭示了傅玄诗歌“新温婉丽,善言儿女”的特点,但说他“怀情正深”,却未必正确。这类诗多是一般性的言情,很少能看到作者的情怀,这也就是为何傅玄只以乐府诗的形式,来写言情诗的主要原因。一些描写爱情的小诗有着较高的艺术成就,如《杂言》:“雷隐隐,感妾心;倾耳听,非车音。”仅仅十二个字,却传神地表现了思妇如痴入迷的情态。有些诗纯系机械的模拟之作,开西晋诗重模拟之先河,但这类作品艺术性普遍不高。
二、张华
字茂先,出身寒微而官至显位。张华写男女相思离别之情,不象傅玄那样只写乐府诗,《情诗》五首是代表作。钟嵘评张华诗“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诗品》);何焯认为张华除《励志诗》外,“余皆女郎诗也”(《义门读书记》卷四),显然都有些以偏盖全,毕竟张华还有《轻薄篇》、《游猎篇》、《壮士篇》这些讽戒现实的作品。但对于这组诗来说,二人的评价无疑是正确的。傅玄完全是站在女性的角度来写情的,张华的《情诗》则从男女双方不同的角度,将绵绵的情思展示得无比生动。第一首与第四首从女子的角度来写。第二、三、五首都是从男子的角度来写的。总的来看,张华的《情诗》五首,不离传统的相思离别主题,细腻深沉和清丽朗畅是其成功之处,但与傅玄的言情诗一样,缺少诗人自身的情感体验。
第二节 太康文学
西晋太康(武帝280--290)、元康(惠帝291--300)时期,文坛上出现了更多的作家,有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之称。其主要成就仍然表现在诗歌方面。由于时代的原因,太康诗歌不可能唱出建安诗歌的慷慨之音,也不会写出阮籍那种寄托遥深的作品,总体来说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抒情强烈;二是形式上拟古;三是技巧进步但诗风繁缛(本指繁密而华茂,后用以比喻文采过人。分而言之,繁,指描写繁复、详尽,不避繁琐。缛,指色彩华丽。《说文》曰:“缛,繁彩也”)。相比较而言,左思的诗歌算是一个例外。
一、陆机
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祖父陆逊为吴丞相,父陆抗为东吴名将、大司马,地位显赫。东吴被灭时,陆机20岁,与弟陆云退居旧里,闭门读书,九年后以文才被召入洛阳,很受北方士大夫的器重。
陆机作为客居异乡谋取前程的游子,其功名心与恋土情都是非常强烈的,二者常常纠结在一起,令诗人难以释怀。思念故土的情怀,通常是在眷恋功名而又未知前途吉凶的彷徨心态下产生的。如《赴洛道中作》其一:
总辔登长路,呜咽辞密亲。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行行遂已远,野途旷无人。……悲情触物感,沉思郁缠绵。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
陆机在一些辞赋的序言中,以更真实的笔触,记录了他的内心世界,怀土思归之情跃然纸上。如《怀土赋序》:“余去家渐久,怀土弥笃。方思之殷,何物不感?曲街委巷,罔不兴咏;水泉草木,咸足悲焉。” 陆机的恋土情始终与功名心纠结在一起,思归而未能归的根本原因,还是强大的功名心的驱使,他曾说过:“但恨功名薄,竹帛无所宣”(《长歌行》),可谓道出了诗人的心曲。他在临当就刑前,发出了“华亭鹤唳,岂可复闻”的慨叹,表明此刻其功名心才完全被恋土情所取代,这是陆机人格的悲剧。
太康时期,摹拟《诗经》、汉乐府和《古诗》,成为一时风气。陆机也不例外,他还在理论上对于摹拟的创作方式给予了肯定:“或袭故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这里的“袭故”,不能片面理解为拟古。所谓的“故”,就是故旧之意,对于文学而言,一切已经问世的作品,相对于正在创作的作品来说,均可视之为“故”。陆机将“袭故”即摹拟看作一种正常的创作现象,但同时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要在摹拟中有创新,这才是“袭故”的最终目的。“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就是对“袭故而弥新”的进一步解释。陆机的《拟古诗》十二首,基本上都是拟《古诗十九首》的,在内容上皆沿袭原题,格调上变朴素为文雅,显示出诗歌文人化的倾向,其总体水平不及原作。
钟嵘称陆机五言诗“源出于陈思,才高词赡,举体华美”(《诗品》)。试比较以下两首诗:
门有万里客,问君何乡人。褰裳起从之,果得心所亲。挽赏对我
泣,太息前自陈。本是朔方土,今为吴越民。行行将复行,去去适西
秦。 (曹植《门有万里客行》)
门有车马客,驾言发故乡。念君久不归,濡迹涉江湘。投袂赴门
涂,揽衣不及裳。抚膺携客泣,掩泪叙温凉。借问邦族间,恻怆论存
亡。亲友多零落,旧齿皆凋丧。市朝互迁易,城阙或丘荒。坟垅日月
多,松柏郁茫茫。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长。慷慨惟平生,俯仰独悲
伤。 (陆机《门有车马客行》)
虽然曹植的诗歌也有“词采华茂”的特点,但这首诗却较为完整的保留了汉乐府平实流畅的风格,句式简单,没有过多的描绘,在抒情上也十分内敛。陆机此诗的题旨与曹植完全相同,但无疑加大了描写和刻画的力度。从篇幅来看,写主闻客来,曹植仅用了四句,陆机则用了六句;写主客对话,曹植用了六句,陆机则用了十句。从句式上来看,曹植是用了一组对偶:“本是朔方士,今为吴越民”,语言平易,口语色彩浓厚;陆机则用了两组对偶:“亲友多零落,旧齿皆凋丧。市朝互迁易,城阙或丘荒。”不惟对偶工整,语句的雕饰亦十分明显。通过这两首诗的比较,可以肯定,在诗歌形式的安排和句式的剪裁上,陆机比曹植更为用心。
由于陆机的诗歌过分注重于修辞,雕琢太重,难免造成繁冗乏力的毛病。前人对此多有讥评,《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张华对陆机的批评说:“人之作文,患于不才;至子为文,乃患太多也。”沈德潜说,到了陆机,“西京以来空灵矫健之气不复存矣”(《古诗源》)。应该说,诗歌的发展并不是一条直线,我们更需要注意到陆机在语言艺术上的创造力。他很强调物候对感情的引发作用,其诗写景成分也特别多,而且意象描绘得工巧细致。如“轻条象云构,密叶成翠幄”(《招隐诗》),“崇云临岸骇,鸣条随风吟”(《猛虎行》),“和风飞清响,鲜云垂薄阴”(《悲哉行》)等等,以极其敏锐的感受力和丰富的艺术表现力为诗篇增加了美感。
二、潘岳
字安仁,其文风在追求绮丽、喜欢铺写等方面与陆机一致。南朝人论潘、陆之别,多认为潘较和畅,陆则深芜。这是因为潘岳的作品用语较浅,不像陆机那样深奥,文句的连接也比较紧密。但他也很少写出陆机那样精美工致、深于刻炼的句子,在语言的创造方面稍逊。其诗文均以善叙悲哀之情著称,不但为自己写,还常常代别人写。诗歌的代表作有《悼亡诗》三首,以绵绵的哀思,表达了对于亡妻杨氏的怀念。其一写丧妻后的悲痛之情:
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黾勉恭朝命,回心反初役。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帏屏无仿佛,翰墨有馀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怅恍如或存,周惶忡惊惕。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春风缘隟来,晨霤承檐滴。寝息何时忘,沉忧日盈积。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
“帷屏”四句,睹物思人,物是人非,随着空间场景的逐一呈现,诗人的思念之情也不断加深;“春风”四句写沉浸于悲哀之中不觉冬去春来的感受,时间在流逝,哀情却越加沉重。其二、其三虽然描写的具体情景有所变化,但总的意思与第一首相近,显得重复。清人陈祚明说:“安仁情深之子,每一涉笔,淋漓倾注,宛转侧折,旁写曲诉,刺刺不能自休。夫诗以道情,未有情深而语不佳者;所嫌笔端繁冗,不能裁节,有逊乐府古诗含蕴不尽之妙耳。”(《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后人以“悼亡”为题专写亡妻,大体是受其影响。
潘岳又“善为哀诔之文”,《文选》中收录了五篇,王隐《晋书》也称他“哀诔之妙,古今莫比,一时所推”。其《哀永逝文》也写对于亡妻的怀念:
昔同涂兮今异世,忆旧欢兮增新悲。谓原隰兮无畔,谓川流兮无岸。望山兮寥廓,临水兮浩汗。视天日兮苍茫,面邑里兮萧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欢哀兮情换。
写丧失妻之后,觉得周围一切都变得空旷萧条,哀情曲折而深入。《悼亡赋》同样写丧妻之痛,这种以诗、文、赋三种文体追念亡妻的方式,在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潘岳可谓一往而有深情者也。不过,潘岳对亡妻的深情与对爱情的坚贞不移,还是有所区别的。罗宗强先生根据挚虞的《新婚箴》和潘岳的《答挚虞新婚箴》,指出:“他对他的妻子的感情,是一种强烈的男女之爱,而不是一种有着道德准则制约的专一的爱。这种爱是建立在女色的美的吸引力之上的,是男女爱悦之情。”(《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由此,我们可以更深入地认识西晋士风影响下的情爱观。
三、左思
字太冲,出身于寒素家庭。妹左芬以文才被召入武帝内宫,左思随之移家洛阳。曾为权臣贾谧门下“二十四友”之一,并曾为贾谧讲《汉书》。入京之初,他自然也有求取仕进的企图,却为门阀制度所阻遏,官止于秘书郎。他最后终于退出了官场,而将满腔不平,写在八篇一组的《咏史诗》中。
《咏史诗》中,有的表达对门阀制度的不满,如其二: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涧底之松,纵然高大挺拔,可是生于卑下之所,竟被山顶的小苗所遮盖。社会也是如此,寒士无所凭依,纵然“英俊”,也只能沉沦下僚。这是门阀制度造成的,并且由来已久。
有的表现对豪右的蔑视和对寒士自身价值的肯定,如其六:
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震。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
赞扬了荆轲、高渐离等卑贱者慷慨高歌、睥睨四海的精神,表达了对豪门权贵的蔑视。最能表现左思气概的是其五:
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自非攀龙客,何为欻来游?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
这首诗先写宫延和王侯第宅之豪华,接下来用“自非攀龙客,何为欻来游” 将前面的渲染一笔抹倒,对功名富贵表示了极度的鄙弃。他说自己只愿作一位象许由那样的高士。此诗末尾“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二句,是这组诗中的最强音。
以“咏史”为诗题,始于东汉的班固。班固的《咏史》诗,直书史实,钟嵘评为“质木无文”(《诗品序》)。建安时期,王粲、阮瑀有《咏史诗》,曹植有《三良诗》;与左思同时的张协也有《咏史》诗。左思的咏史诗,既受前人的影响,又有一定创新。明代胡应麟说:“太冲《咏史》,景纯《游仙》,皆晋人杰作。《咏史》之名,起自孟坚,但指一事。魏杜挚《赠毋丘俭》,叠用八古人名,堆垛寡变。太冲题实因班,体亦本杜,而造语奇伟,创格新特,错综震荡,逸气干云,遂为古今绝唱。”(《诗薮》外编卷二)对咏史诗的流变及左思《咏史诗》的价值,概括得相当准确。清人何焯则认为左思的《咏史》诗是变体:“咏史者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隐括本传,不加藻饰,此正体也。太冲多自摅胸臆,乃又其变。”(《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从咏史诗的发展先后顺序来看,以“隐括本传”者为正体,以“自抒胸臆”者为 “变体”,并不为错,然而左思之“变体”,成就远远超过了前人的正体。
钟嵘《诗品》置左思于上品,评其诗曰:“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他的诗多引史实,故曰“典”。借古讽今,对现实政治持批评态度,故曰 “怨”。而借古讽今又能做到深刻恰当,故曰“精切”。他的诗能起到讽谕作用,故曰“得讽谕之致”。钟嵘《诗品》还说左思的诗“出于公干(刘桢)”;在论及陶渊明时则说“又协左思风力,”他标举“左思风力”,含有左思再现了建安风骨的意思,这是很有道理的。
左思的咏史“或先述己意,而以史事证之。或先述史事,而以己意断之。或止述己意,而史事暗合。或止述史事,而己意默寓”(张玉谷《古诗赏析》),又往往错综史实,连类引喻,名为咏史,实是咏怀。这是对咏史诗的创造性的发展,对后代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所以前人评云:“创成一体,垂式千秋。”(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
左思的《娇女诗》是一首叙事诗,写大女儿惠芳和小女儿纨素日常生活中的趣事,充分发挥了五言诗言情写物的功能,虽以叙事为线索,但大段的描写成为诗歌的主干:
小字为纨素,口齿自清历。鬓发覆广额,双耳似连璧。明朝弄梳台,黛眉类扫迹。浓朱衍丹唇,黄吻澜漫赤。……其姊字惠芳,面目灿如画。轻妆喜楼边,临镜忘纺绩。……从容好赵舞,延袖象飞翮。上下弦柱际,文史辙卷襞。
二女的娇憨可人,天真活泼,正是通过这些描写性的文字展示出来的,而字里行间透出的是慈父的无限怜爱之情,全诗洋溢着浓厚而又温馨的家庭气氛。值得注意的是,五言诗从产生以来,还没有看到抒写父辈和子女间天伦之乐的作品。左思首次将这一题材引入五言诗,扩大了言情的范围,对后世诗歌产生了很大影响。东晋陶渊明的《责子》,以自嘲的口吻,描绘了五个儿子的习性和身为人父的感受。唐代杜甫的《北征》和李商隐的《骄儿诗》,沿用五言古体写父子之情。左思的开创之功,不可忽视。
左思的《三都赋》,有“洛阳纸贵”之誉。但在魏晋辞赋已经完全转向抒情短篇的情况下,它终究无力重振传统大赋的声威。
第三节 刘琨与郭璞
一、刘琨
字越石,早年好老庄,喜清谈,也是贾谧“二十四友”之一。后来天下大变,他经历国破家亡,意识到个人对于社会、政权的责任感,于是指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答卢谌书》),这是时代造成的思想改变。他和祖逖闻鸡起舞的故事更经常为后来一些富有事业心的学者、诗人所称道。他在外族入侵的情况下,历任刺史、大将军等职,在北方辗转抗敌,后因军事失利,投幽州刺史段匹磾,竟为段所害。刘琨仅凭一腔热血出生入死,面对中原瓦解之势,自知只手擎天,绝无此理。家国之痛,英雄末路之悲,发之于诗,既慷慨激昂,又沉痛无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扶风歌》是刘琨的代表作之一。永嘉元年(307)他任并(平声,指山西)州刺史,募兵千馀人,“以少击众,冒险而进,顿伏艰危,辛苦备尝”, 历尽艰辛才到达任所晋阳,诗写途中经历和激愤、忧虑之情:
朝发广莫门,暮宿丹水山。左手弯繁弱,右手挥龙渊。顾瞻望宫阙,俯仰御飞轩。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系马长松下,发鞍高岳头。烈烈悲风起,泠泠涧水流。挥手长相谢,哽咽不能言。浮云为我结,归鸟为我旋。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麋鹿游我前,猿猴戏我侧。资粮既乏尽,薇蕨安可食。揽辔命徒侣,吟啸绝岩中。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穷。惟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弃置勿复陈,重陈令心伤。
刘琨被段匹磾拘时写了《答卢谌》和《重赠卢谌》,是刘琨的绝命诗。《诗品》评刘琨诗:“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文心雕龙》说刘琨诗“壮而多风”,都是指诗中激荡而深沉的感情而言。这恰是西晋一般诗人所缺少的。元好问《论诗绝句》说:“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
二、郭璞
字景纯,博学多识,为时人所重。又喜阴阳卜筮之术,因此关于他有很多怪诞的传说。例如他看上庐江太守的婢女,施法术将她弄到手中。西晋末北方乱起,郭璞南下避祸。东晋元帝时任著作郎。后因劝阻王敦谋反,被杀。传说他分别为温峤、瘐亮和王敦占卜,有意倾向于前者,激怒了后者。
郭璞的代表作是《游仙诗》,今存19首,其中有9首为残篇。游仙诗的来源很早,秦博士有《仙真人诗》,汉乐府中也有这类作品,建安、正始时期更不断有人继作。游仙诗中明显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所谓正格的游仙诗,它们“滓秽尘网,锱铢缨绂,餐霞倒景,饵玉玄都”(《文选》李善注);一种是借游仙以表示对现实的不满与反抗,如曹植、阮籍的某些作品。郭璞显然是继承了后一种传统。钟嵘《诗品》说他的《游仙诗》“辞多慷慨,乖远玄宗”,“坎壈咏怀”,这是很确切的评价。他的《游仙诗》写隐居高蹈,乃是仕宦失意的反映,而非如道家之鄙弃仕途;他所抒发的不是庄子的那种逍遥精神,而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他的游仙是其仕途偃蹇、壮志难酬时的精神寄托,是抒发其苦闷情怀的一种特殊方式。
《游仙诗》的第一、二首,集中写其隐逸之情,如其一:
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栖。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临源挹清波,陵冈掇丹荑。灵溪可潜盘,安事登云梯?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藩羝。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
此诗写仕宦之求不如高蹈隐逸,山林之乐胜于求仙。隐居高蹈,可以保持品德完好和自身的自由;退回尘世,则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最能显示其“坎壈” 之怀的是第五首:
逸翮思拂霄,迅足羡远游。清源无增澜,安得运吞舟?珪璋虽特达,明月难暗投。潜颖怨青阳,陵苕哀素秋。悲来恻丹心,零泪缘缨流。
《游仙诗》也有几首是写神仙世界的,但多别有怀抱,
西晋后期至东晋初年,孙楚、潘尼、曹摅、枣腆诸人之诗,玄理渐多,故钟嵘说其“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品》)。关于郭璞与玄言诗的关系,有两种相反的说法。檀道鸾《续晋阳秋》说:“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这等于说郭璞是玄言诗的倡导者。然而钟嵘《诗品》却说郭“始变永嘉平淡之体”。这一矛盾现象,与郭璞诗的特点有关。如果从缘情寄兴的一面看,颇与所谓“永嘉平淡之体”相背,显得卓拔时俗;如果从好言老庄哲理和假游仙以倡虚寂的一面来看,却又像是玄言诗的前导了。所以檀道鸾和钟嵘各从一面着眼,就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但无论如何,不应将郭璞的《游仙诗》等同于玄言诗。故刘勰说其“足冠中兴”,钟嵘评为“中兴第一”。
郭璞借游仙写其坎壈之怀,继承了《诗》、《骚》的比兴寄托传统。朱自清说:“后世的比体诗可以说有四大类。咏史,游仙,艳情,咏物。”“游仙之作以仙比俗,郭璞是创始的人。”(《诗言志辨·比兴·赋比兴通释》)的确,郭璞以游仙写失意之悲,与左思借咏史抒牢骚不平,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四节 东晋玄言诗
一、玄言诗的盛行
魏晋玄学的出现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现象。从文学范围来说,玄学对于诗歌领域的影响是最为明显的,主要表现在直接以玄理入诗以及玄学思维方式对诗歌创作的影响等两个方面。在诗歌中时或阐说和体悟玄理的现象,自玄学产生后,在何晏等人那里就已经开始出现。随着玄学的发展和谈玄风气的日益兴盛,以诗歌来阐说和体悟玄理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永嘉(怀帝307-312)时,玄学清谈十分盛行,南渡后,势力有增无减。士人为了在心理上逃避惨痛的现实,普遍将热情贯注于哲学领域,对文学尤其是诗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形成了所谓的“玄言诗”。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王钟陵的《玄言诗研究》一文,对玄言诗的概念界定、发展流变以及艺术特征等问题,做出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由此拉开了新时期魏晋玄言诗研究的序幕。此后,针对玄言诗内涵的界定、玄言诗发展阶段等问题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如对玄言诗发展阶段的认识迄今仍未达成共识,但对于玄言诗的界定,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王钟陵指出:“凡是以体悟玄理为宗旨的诗概属于玄言诗。体悟玄理有两条途径:一是直接从理性入手,二是从感性形象入手。前一条途径形成枯燥的说理诗,后一条途径则能够产生一些将一定的感性形象和一定的理性内容结合起来的篇什。”
玄言诗在东晋也经历了一个由初起到兴盛及至最后衰退的阶段。初期的玄言诗人应以卢谌和庾阐为代表。从卢谌现存作品来看,诗歌中往往将身世之感与对玄理的体悟交织在一起,与东晋中期典型的以体悟玄理为宗旨的玄言诗还是有所区别。庾阐的诗歌中经常出现对山水景物的描写,借助于山水景物来体悟玄理,是其诗歌的突出特征。经过东晋最初三十年左右时间的发展,玄言诗很快进入最为兴盛的时期。这时期写作玄言诗的诗人和诗作都应为数不少,最有代表性的诗人当属孙绰和许询。此外,兰亭诗人是以玄思对山水,自然景物虽然出现在诗中,但并不是作为一个审美对象而被欣赏的,它至多只是一个载体。从这个角度说,兰亭诗仍然是标准的玄言诗。玄言诗大抵在东晋后期开始出现式微之势。檀道鸾说:“至义熙中,谢混始改。”钟嵘说:“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沈约也说:“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孝武帝376-396)之气。”义熙是东晋安帝的年号(405-418),也就是说,玄言诗流行诗坛的局面是到了东晋义熙年间才得到改观的。玄言诗在东晋末年逐步衰退之后,到了南朝刘宋初年,基本上退出了诗坛。刘勰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 南朝谢灵运山水诗已经是山水审美意识走向成熟的典型代表,但他的山水诗中还是常常夹带抒写玄理的诗句,到了谢朓才基本上清除了玄言的痕迹。
南朝文论家在谈到玄学与诗歌的关系时,往往着眼于其负面影响,强调玄风弥漫与诗歌的枯燥乏味。钟嵘《诗品序》说: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
《文心雕龙·时序》云:
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由于清谈)余气(风气),流成文体(造成新的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艰难),而辞意夷泰(平静),诗必柱下之旨归(思想),赋乃漆园之义疏(注解)。
可以说,在玄学影响诗歌所形成的主要特征等问题上,两人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
二、孙绰、许询的玄言诗
在历时一百多年的玄言诗史上,其鼎盛阶段当属东晋成帝(325-342)至哀帝(362-365)所统治的几十年间,而孙绰与许询是当时最知名的两位诗人。《晋书·孙绰传》载:“绰少以文才垂称,于时文士,绰为其冠。”《世说新语·品藻》亦载:“支道林问孙兴公:‘君何如许掾(询)?’孙曰:‘高情远致,弟子蚤已服膺;一吟一咏,许将北面。’”从这两条文献可以看出,孙绰在当时是颇富盛名,同时也是极为自负的,其《秋日诗》:
萧瑟仲秋月,飚唳风云高。山居感时变,远客兴长谣。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霄。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抚菌(《庄子·逍遥游》:“朝菌不知晦朔”)悲先落,攀松羡后凋。垂纶在林野,交情远市朝。澹然古怀心,濠上岂伊遥。
这是一首写景咏怀的佳作,诗人面对仲秋时节萧条的景物而心生感慨,表达了对逍遥的林野生活的向往。虽然多处引用《庄子》的事典,可非但没有枯燥的说理,即便是玄思,也淡得近乎不见。或者说,其玄思已经化为景物了。
许询与孙绰“并为一时文宗”(《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世说新语·文学》载:“简文称许掾云:‘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说明许询的五言诗在当时有相当大的影响。但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有一首《竹扇诗》和两首各为两句的残篇,遗佚之甚,可想而知。
三、王羲之与兰亭唱和
王羲之,字逸少,琅琊临沂人,居会稽山阴,王导从子。官至右军将军,世称王右军。他虽出身高门,却淡薄宦情,好隐居,与清谈名士交游,以山水吟咏为乐。《晋书·王羲之传》说他:“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至。”浙江绍兴至今还有王羲之的一些遗迹。当年,右军别业被王羲之舍宅为寺,初为“昌安寺”,唐代后改为“戒珠寺”,寺前今尚存墨池。寺南150米左右,今尚有题扇桥、躲婆弄等遗迹。
东晋诗人与山水结下了不解之缘,体玄悟道相当程度上就是借助于自然山水来完成的。这时期出现的兰亭雅集,实在可以说是文坛上的一件盛事。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五十一岁的王羲之任会稽内史,三月三日这天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会集于此,饮酒赋诗。聚会的起因源于“修禊”这一习俗。古人于三月上旬巳日,在东流水洗濯,祓除不祥。后来发展为暮春之初在水边宴饮嬉游,祓除不祥的意义反而退居其次,兰亭之会就是如此。为了增加趣味,采取流觞赋诗的方法,流觞所至,即席赋诗。作诗的规矩当是每人作四、五言诗各一首。此次聚会,王羲之、谢安、孙绰等11人成四、五言诗各一首;郗昙、王玄之等15人各成诗一首;谢瑰、王献之等16人诗不成,罚酒三觥。共得诗37首,其中五言诗23首,四言诗14首,编为《兰亭集》。王羲之除了写诗以外,还作了一篇序文,即《兰亭集序》,记述此次盛会,更多地是抒发当时的内心感受。其文曰: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孔子语),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此序的前半记述这次盛会概况,写山水之美,饮酒吟咏之乐,以一“乐”字为基调,行文自始至终从容沉稳,模山范水,语言简洁,层次清晰,可谓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一应俱全。后半由眼前之乐想到人生短促,以一“悲”字相贯穿。俗话说“盛宴必散”,由此带来的感伤,更具有感动人心的力量。
此前石崇于西晋元康六年(296),在他的金谷别业为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还长安送行所举办的雅集活动,也有三十人参加,“昼夜游宴”,“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唱和诗作编为《金谷诗》。石崇在《金谷诗叙》中先叙众人宴集之乐,接着写“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潘岳今存《金谷集诗》一首。此后王勃《滕王阁序》也发出了“呜呼!胜地不常,盛筵难再。兰亭已矣,梓泽丘墟”的慨叹,真可谓人同此感。
兰亭诗的内容,或抒写山水游赏之乐,表现山水审美的情趣;或由山水直接抒发玄理。王羲之《兰亭诗》云:“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仰望碧天际,俯瞰绿水滨。……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诗人在碧天绿水中充分体悟到了庄子齐物的哲学理论,造化不诬,自然万物虽然千差万别,却都以各自的方式合理地存在着,由此,群籁固然参差,又无不新人耳目。除了山水与玄理相结合以外,兰亭诗还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即篇幅短小。二十三首五言诗中,五言四句者有十五首,五言八句者有七首。四言的兰亭诗也多为四句或八句。
总的来说,兰亭诗无论是写山水还是写玄理,艺术水平都不高,但标志着诗人已开始留意山水审美,并从山水中体悟玄理。这种尝试预示着山水诗将要兴起。兰亭雅集对中国文人生活情趣有重大影响(韩国庆州有鲍石亭,内有新罗时代曲水流觞的遗迹),同时对诗歌流派的形成也有推动作用。
四、玄释合流
东晋玄言诗的发展,与佛教的流行大有关系。王导、谢安、简文帝、孙绰、许询、王羲之、殷浩等人与名僧支道林、竺法深、释道安、竺法汰等过从甚密,佛学与玄学受到同样的尊重。僧人参与文人名士的谈玄活动,文人名士研习佛经或参与佛事活动,僧人与文人名士畅游山水的活动。名士如孙绰、许询皆精通佛理,名僧支遁等又深于老庄之学,玄佛互相渗透。《世说新语·文学》记载“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即后来的简文帝)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另外,名士孙绰曾作《道贤论》,以“竹林七贤”配七位名僧。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虽然现存支遁诗歌中没有反映与众人同咏山水的作品,但与文人名士的登临山水,使他的一些诗作如《咏怀诗》五首其四或多或少还是染上了山水的印记,前人往往将支遁此类诗歌视作谢灵运之先声,自有其道理。
慧远在庐山修行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僧俗弟子往来者甚众,后人习惯以“莲社”称呼这个群体,或许因“彼院多植白莲,又弥陀佛国以莲华分九品次第接人,故称‘莲社’”。他与刘遗民、宗炳、雷次宗等文人多有交往,僧俗群体也曾有过游山赋诗活动,如慧远《庐山东林杂诗》、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借山水阐说玄佛义理。
五、湛方生的山水佳作
东晋后期的湛方生无疑是永嘉南渡以来,善写山水诗的最大家,虽然其生平思想至今难以说清,但其留下的几首描写山水的五言诗,却是东晋诗坛上的绝佳之作。如《帆入南湖》:“白沙净川路,青松蔚岩首。此水何时流?此山何时有?人运互推迁,兹器独长久。悠悠宇宙中,古今迭先后。”诗中写景不多,“白沙”、“青松”两句极简洁、极清拔,诗人由水流山在而引发的近乎天真的设问,实则蕴涵了无穷的哲理,此理绝非玄佛义理,而是饱含着深邃的宇宙情怀。又如《还都帆诗》:
高岳万丈峻,长湖千里清。白沙穷年洁,林松冬夏青。水无暂停留,木有千载贞。寤言赋新诗,忽忘羁客情。
首二句写高山长湖,境界极为阔大;“白沙”两句看似写景,实则景中寓理;“水无”二句,是对前两句的进一步补充。诗人道出了自然永恒之理,在寄心山水的同时,也就了然忘怀世情了。
这两首诗是通过寓目山水而即情述理的,然而与一般的玄言诗借山水阐发玄佛义理完全不同,虽不能说为诗坛洗尽玄风,但至少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革除了玄言诗平典晦涩的弊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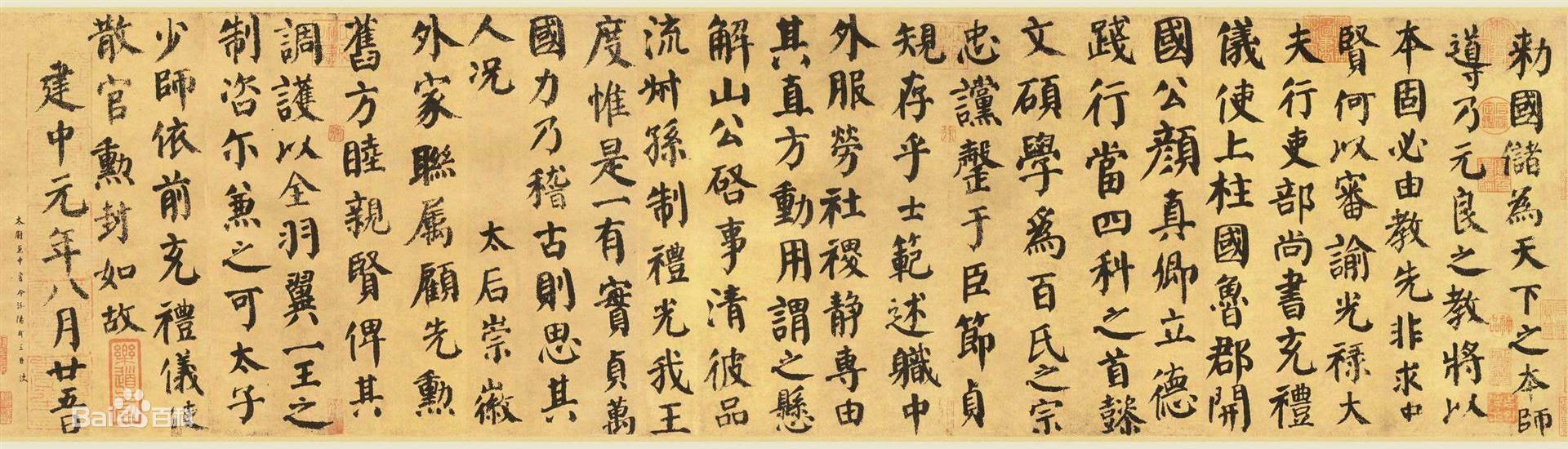
 第一章(建安文学).ppt
第一章(建安文学).ppt
 2、第二章(两晋文学).pptx
2、第二章(两晋文学).pptx
 3、第三章(陶渊明).pptx
3、第三章(陶渊明).pptx
 第四章(南朝文学).ppt
第四章(南朝文学).ppt
 第五章(北朝文学).ppt
第五章(北朝文学).ppt
 第六章(六朝小说).ppt
第六章(六朝小说).ppt
 1、绪论、第一章 隋代文学.ppt
1、绪论、第一章 隋代文学.ppt
 1、绪论、第一章 隋代文学.ppt
1、绪论、第一章 隋代文学.ppt
 3、第三章 盛唐文学.pptx
3、第三章 盛唐文学.pptx
 3、第三章 盛唐文学.ppt
3、第三章 盛唐文学.ppt
 4、第四章 李白.pptx
4、第四章 李白.pptx
 5、第五章 杜甫.pptx
5、第五章 杜甫.pptx
 6、第六章 中唐文学.pptx
6、第六章 中唐文学.pptx
 2、第二章 初唐文学.pptx
2、第二章 初唐文学.pptx
 2、第二章 初唐文学.ppt
2、第二章 初唐文学.ppt
 7、第七章 唐传奇与笔记小说.ppt
7、第七章 唐传奇与笔记小说.ppt
 8、第八章 晚唐文学.ppt
8、第八章 晚唐文学.ppt
 9、第九章 唐五代词.pptx
9、第九章 唐五代词.ppt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