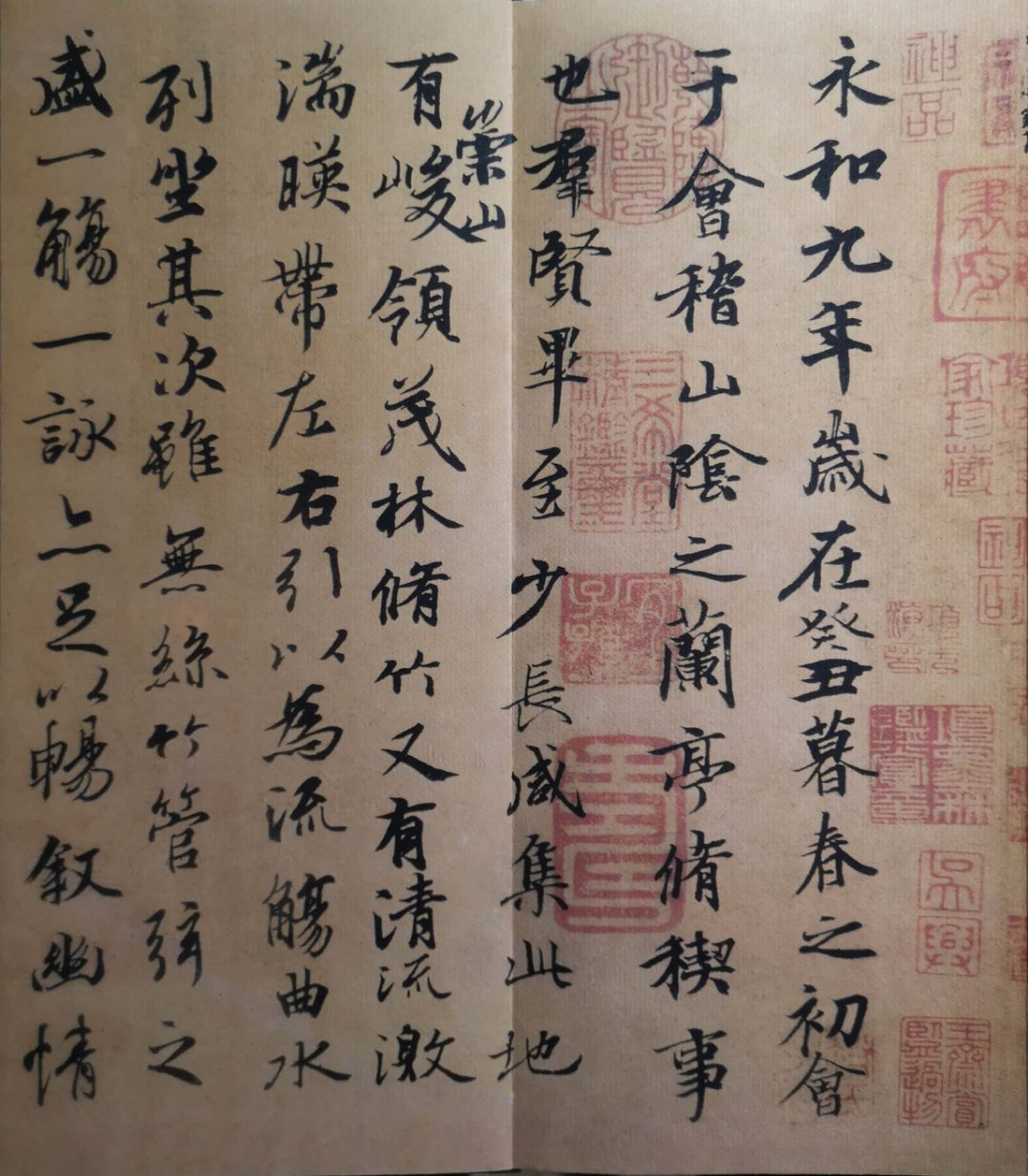第六章 侠文化与六朝文学
(一)、侠之身份辨析
历史文献中对侠的称谓较多,如“游侠”、“任侠”、“豪侠”、“气侠”、“轻侠”、等等,这里“游”、“任”、“豪”、“气”、“轻”虽指出了侠的某种特质,但并无根本区别。在今知最早记录侠的文献《韩非子》中使用了“游侠”一词(《五蠹》:“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其后《史记》、《汉书》中又均有《游侠列传》,因此游侠便成为侠的代名词。
侠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是否真的存在过?如果有,这又是怎样的一个群体?也就是说侠的身份是什么?这似乎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了,但学者们各执己见,至今也没有得出令大家都信服的结论。有学者以为所谓的游侠不过是一群具有侠客气质的人,而并非什么特殊的社会集团(日本增渊龙夫1952年,此后刘若愚《中国之侠》有进一步补充,认为“他们是具有强烈个性,为了某些信念而实施某些行为的一群人”),以此来否定侠的实存性,显然是不够客观的,至少《史记》、《汉书》中诸多游侠传记足以证明。此外,围绕游侠的社会身份所出现的争议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种观点认为游侠来自于平民和破落武士(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补》31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杨联升1957年),主要由各类游民、门客、武士、刺客构成,若追溯其源头,当与墨家有一定联系。多以韩非子所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为依据,认为游侠乃“私剑”即带剑之客,而为主上所养。《史记集解序》司马贞索引:“游侠,谓轻死重气,如荆轲、豫让之辈也。”也成为人们将刺客纳入游侠群体的依据。
另一种观点认为游侠是“盛养门客,食客,刺客者”(钱穆),进而将游侠与刺客和某些门客等私剑群体明确区分开来。其主要依据是《史记》与《汉书》所立《游侠列传》中对战国四公子作为卿相之侠的肯定及诸游侠皆盛养宾客的记载(参见钱穆《释侠》,《学思》第一卷第三期)。为进一步论证此观点的正确性,亦有学者对前引韩非子的话做了新的诠释,指出韩非子“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这句话的本义为“群侠以(其)私剑养”,“私剑”即私门之剑,也就是游侠所盛养的宾客、刺客等。(参见章培恒《从游侠到武侠》复旦学报1994年3期)。
总的说来,造成两种观点的分歧,主要在于对历史文献的择取与解读。《韩非子 五蠹》中关于游侠的一段文字,既然在阐释上有模糊性,就不足以作为游侠真实身份的依据。在这种情况下,汉代史料文献中的记载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二)、汉代游侠群体与任侠行为考察
虽然两汉统治者出于大一统王朝的安定对地方豪侠进行过严厉打击,但汉代的游侠群体从未完全消失,“郡国处处有豪桀”(《汉书 游侠列传》)的现象直到东汉依然存在,这也是侠文化得以延续下来的保证。根据史料记载,汉代游侠群体主要在三个时期较为活跃。
首先是西汉建国之初至武帝时期。汉初战国遗风尚存,而朝廷“禁网疏阔”(《汉书 游侠列传》),加之郡国并行的政治体制,为游侠的活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这时期的权贵之侠以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为代表,布衣游侠以朱家、田仲、剧孟、郭解为代表。他们“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一度对王朝的稳定构成了威胁,在景帝、武帝的多次打击之下逐步式微。
其次是西汉成帝至王莽专政时期。《汉书·尹赏传》载:汉成帝“永始、元延年间,上怠于政,贵戚骄态,红阳长仲兄弟交通轻侠,藏匿亡命。”长安游侠万章也主要活跃在成帝时期,当时“长安炽盛,街闾各有豪侠”(《汉书 游侠列传》)。哀帝、平帝时期,各地游侠层出不穷,王莽秉政期间曾大肆诛杀,“王莽居慑,诛锄豪侠”(《汉书 游侠列传》)。这阶段的游侠与西汉初期有所不同,他们大多为地方官吏,如万章为京兆尹门下督,楼护早年“为京兆吏数年,甚得名誉”,后为天水太守、广汉太守,陈遵初为京兆史,后为河南太守等等,完全可以称之为官吏之侠。这种转变,自然与朝廷对地方豪侠打压力度加大使其转而寻求以为官来避祸有关,如原涉“宾客多犯法,罪过数上闻。王莽数收系欲杀,辄复赦出之。涉惧,求为卿府掾史,欲以避客。”(《汉书 游侠列传》)此外,也与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世间普遍追求功名的风气有关。
再次是东汉末年,政权风雨飘摇,各路豪杰纷起,袁绍、董卓均可谓公族豪侠,袁绍“素善养士,能得豪杰用,其从弟虑贲中郎将(袁)术亦尚气侠。”(《后汉书》卷69《何进列传》)董卓“性粗猛有谋。少尝游羌中,尽与豪帅相结,……以健侠知名”(《后汉书》卷72《董卓列传》)张邈少以侠闻,常振穷救急,“董卓之乱,与曹操共举义兵”。(《后汉书》卷75《张邈列传》)这个时期的游侠,多为地方豪强,其善养士、结私交的特点与西汉时期的游侠颇为相似,不过他们大多是以此作为自己日后争霸的资本。
《汉书·季布传》颜师古注曰:“任,为任使其气力。侠之言挟也,以权力侠辅人也。”汉代游侠的任侠行为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振穷济困,以义服众。
其次,轻死重气,快意恩仇。
再次,持吏长短,对抗官府。
对于汉代游侠的诸种任侠行为,司马迁和班固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给予了评判。前者发现了游侠身上的美德,认为“其行虽不轨於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史记》游侠列传)“救人於戹,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叙》)后者更强调法制对于国家的重要性,认为“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汉书》卷92《游侠列传》)这两种评价真实反映了汉代游侠文化本身的复杂性,相比较而言,荀悦的评价可能更为客观:“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于为盗贼也。”(《汉纪·孝武一》)
(三)、魏晋南北朝“侠出年少”现象分析
在许多人看来,游侠群体在东汉以后就基本不复存在了。即便存在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游侠了。诚然,正如本文前面所述,游侠群体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其身份发生了不小的改变,但毕竟游侠群体并未因此而消亡,这是不争的事实。随着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的改变,尤其是在朝廷的严厉打击下,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西汉朱家、郭解、原涉那样终生以游侠身份行事者极难见到,游侠群体多为年少者组成,而且大部分游侠的身份都是短期行为,而后或折节读书跻身仕途,或为朝廷、地方势力所收纳,成为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
年少任侠者在两汉时期不乏其人,如西汉时期的朱云、眭弘,东汉时期的王涣、张邈等,但似乎只有魏晋以后这种现象才更为集中和突出。兹据文献援引数条如下:
(杨阿若)少游侠,常以报仇解怨为事。(《三国志》卷18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 勇侠传》)
(甘宁)少有气力,好游侠,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三国志》卷55《甘宁传》)
(戴)若思有风仪,性闲爽,少好游侠,不拘操行。(《晋书》卷69《戴若思传》)
(孟龙符)骁果有胆气,干力绝人,少好游侠,结客于闾里。(《宋书》卷47《孟龙符传》)
(周炅)少豪侠任气,有将帅才。(《陈书》卷13《周炅传》)
(裴之横)少好宾游,重气侠,不事产业。(《南史》卷58《裴之横传》)
(毕)元宾,少而豪侠,有武干,涉猎书史。(《魏书》卷61《毕众敬传》)
(慕容)俨少任侠,交通轻薄,遨游京洛间。(《北齐书》卷20《慕容俨传》)
(敬显俊)少英侠有节操,交结豪杰。(《北齐书》卷26《敬显俊传》)
(梁士彦)少任侠,好读兵书,颇涉经史。(《周书》卷31《梁士彦传》)
(韦)法保少好游侠,而质直少言。所与交游,皆轻猾亡命。(《周书》卷43《韦法保传》)
从上引文字可以看出,自三国至南北朝的近四百年间里,侠出年少始终都是较为突出的社会现象。这既说明了游侠文化的延绵不绝,也意味着一定有更为深层的原因存在。
首先,无论从生理学还是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在青少年阶段都还不够成熟,易为新鲜事物所吸引,也易于冲动。结客任侠、复仇杀人在年少游侠们看来是十分刺激和有意义的事。这一点已为学者所注意,“侠义这杆大旗掀动着热血少年的心扉,它通过人的防卫本能和各种渠道内化到意识中,使众多少不经事的复仇参与者事前未遑深虑。他们的犯禁复仇与其说是受伦理规范支配,毋宁说是更多的出自青少年情绪特点,一种潜意识的迸涌加上挺而走险的好奇,以及炫耀勇力和正义的冲动。”(王立《魏晋六朝“年少慕侠”与侠义建功主题》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2期)需要补充的是,除了青少年所特有的生理和心理特点以外,社会风气也起着很大的作用。汉末以来,随着儒学的衰微和玄学的兴起,突破世俗礼制规范、任性而为的叛逆思想在士人尤其是官宦子弟那里成为一种风气。前引西晋时期的戴若思,祖父为三国吴的左将军,父为会稽太守,而他却“好游侠,不拘行操”,率众劫掠陆机财物,后在陆机言语感化下翻然悔悟,终成一番事业。又如王弥,家世二千石,祖父王颀,在曹魏和西晋武帝时分别担任玄菟太守和汝南太守”,而他“少游侠京都”,隐士董仲道评价他“若天下骚扰,不作士大夫矣”。(《晋书》卷100《王弥传》)这种任诞风气俨然一种时尚,会波及到当时社会的各个层面,从而孕育出更多的年少游侠们。
其次,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社会秩序混乱,年少者结客任侠,既是保全自我的一种方式,也是成就功业的一条途径。他们往往通过任侠活动引起一些雄杰之士的注意而被纳为自己的部署,或者是成为朝廷的一支得力的武装力量,有些人还因战功而逐级升迁,扬名天下,这对于年少的游侠们来说未尝不是一种理想的归宿。无疑,这也将作为一段佳话播于人口、留于人心,并不断激励着后来者的效仿。鲁肃曾以自己的号召力招聚了轻侠少年百馀人投靠周瑜(《三国志》卷54《鲁肃传》);史涣年少任侠,有雄气。曹操刚刚起兵,史涣便投靠到他的帐下,做了中军校尉,征战南北(《三国志》卷9《史涣传》);上引北齐时期的慕容俨年少任侠,“交通轻薄,遨游京洛间”,而后跟随朝廷军队征伐每立战功,展现了将帅之才。再如北周时期的陈忻早年在“魏孝武西迁之后,乃于辟恶山招集勇敢少年数十人,寇掠东魏,仍密遣使归附。”(《周书》卷43《陈忻传》)最终为朝廷立下了赫赫战功。
再次,东汉时期开始出现了人物品评制度,至曹魏初期人物品评明显体现了一种政治需求,社会上对人才的渴求决定了人物品评重才轻德的价值取向,如刘邵《人物志》中对于偏才的分析和对历史上英雄人物的评价。在乡党乡议的内容中也会将游侠的某些行为作为正面的品评标准,这在某种程度上会激发年少者结客任侠之风气的形成,故此汉末魏晋时期年少任侠者极多。祖逖年少时“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每至田舍,辄称兄意,散谷帛以周贫乏,乡党宗族以是重之”。(《晋书》卷62《祖逖传》)这种风气直到南北朝时依然不衰,北齐时高乾之父高翼“豪侠有风神,为州里所宗敬”;刘叔宗年少任侠,“为州里所爱”。(《北齐书》卷21《高乾传》)
(四)、侠文化在文学艺术中的呈现
从文化的角度来说,中国历史上的侠应该包括两个群体,一是确实在历史上真实出现过的如前文所述的各类游侠,另一类则是活跃在文艺作品之中的艺术化的游侠形象。两个群体合在一起所构成的侠文化才是充实丰满而有光辉的。事实上,汉代出现的大量的民间谣谚以及司马迁、班固笔下的《游侠列传》,已经让现实生活中真实的游侠走进了文学领域,不过虽然作者流露了较强的主观情感,但总的来说这些形象还都是实录而并非艺术化的。以民间谣谚为例,如“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史记》卷一百《季布栾布列传》载:“季布者,楚人也。为气任侠,有名於楚。……当是时,季心以勇,布以诺,著闻关中。”说明季布的重信守诺在当时是尽人皆知的。
从这个时期侠文化的发展来看,艺术化的游侠形象主要出现在以曹魏以来的诗歌和小说为代表的文学作品之中。限于篇幅,本文仅围绕诗歌作品重点谈两个问题。(《搜神记》和《世说新语》中有反映游侠的作品。)
首先,以曹植的《白马篇》为肇端,虚构的游侠形象奠定了咏侠诗的基本特征。《白马篇》是最早的一首文人咏侠诗: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胡虏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此诗有几点可以注意者:一是以幽并游侠为描写对象,揭示了游侠文化的地域特征。幽、并是指今河北、山西和陕西的部分地区,自汉代以来即游侠辈出,到了魏晋和北朝时期,仍然是游侠出入较多的地区,如西魏时期的毛遐、毛鸿宾兄弟为北地三原人,长期活动在幽州地区(《北史》卷49《毛遐(弟鸿宾)传》);北齐大侠李元忠即为赵郡人(《北齐书》卷22《李元忠传》)。《隋书》卷30《地理志中》载:冀州、幽州地区“俗重气侠,好结朋党,其相赴死生,亦出于仁义”,“太原山川重复,实一都之会,本虽后齐别都,人物殷阜,然不甚机巧。俗与上党颇同,人性劲悍,习于戎马。离石、雁门、马邑、定襄、楼烦、泳郡、上谷、渔阳、北平、安乐、辽西,皆连接边郡,习尚与太原同俗,故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云。”曹植的《白马篇》之后,咏侠诗中多出现幽并游侠的形象,如“六郡良家子,幽并游侠儿”(刘苞《九日侍宴乐游苑正阳堂诗》),“幽并游侠子,直心亦如箭”(吴均《雉子班》),“寄语幽并驰射客”(阳缙《侠客控绝影诗》),“游侠幽并客,当垆京兆妆”(陈叔宝《洛阳道五首》其四),等等。二是彰显了游侠少年高超的武艺,武侠的形象在咏侠诗中得以确立。与两汉时期重视游侠的结交、养客、重义、守诺的品性相区别,魏晋时期对游侠个体的技能和勇力十分重视。鱼豢就曾写过《勇侠传》,专载孙宾硕、祝公道、杨阿若、鲍出四位勇侠。曹植诗中对白马少年高超箭技的描写,亦当受此风气的影响。后代的咏侠诗大多都会利用一定的篇幅来刻画游侠出众的武技,如“吴刀鸣手中,利剑严秋霜。腰间叉素戟,手持白头镶。腾超如激电,回旋如流光。”(张华《博陵王宫侠曲二首》其二)“插腰铜匕首,障日锦屠苏。鸷羽装银镝,犀胶饰象弧。近发连双兔,高弯落九乌。”(刘孝威《结客少年场行》)“白玉鹿卢秋水剑,青丝宛转黄金勒。复有鱼目并龙文,蹑影追风本绝群。影入吴门疑曳练,形来西北似浮云。”(阳缙《侠客控绝影诗》)等。三是抵抗外侮、报效国家的豪迈情怀,是文人追求功业的思想意识的流露。游侠自问世以来就是以“不轨于正义”甚至与朝廷相对抗的面目出现的,然而在《白马篇》中的游侠少年却摇身一变成为驰骋边塞、为国杀敌的英雄。如若结合魏晋以来年少任侠者多通过建立战功而为朝廷所用并最终成就功名的事实来看,此诗中白马少年“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的现实处境与“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英雄气概,就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了。当然,曹植在这首诗中所要表现的主旨还不仅于此,白马少年也是诗人所期盼的自身的理想写照。这种情况在后来的咏侠诗中也经常见到,如“一朝许人诺,何能坐相捐?飘节去函谷,投佩出甘泉。嗟此务远图,心为四海悬”(袁淑《效子建白马篇》);“勒石燕然道,凯归长安亭。县官知我健,四海谁不倾?但使强胡灭,何须甲第成”(孔稚珪《白马篇》);“年少多游侠,结客好轻身。代风愁枥马,胡霜宜角筋。羽书劳警急,边鞍倦苦辛。……男儿重意气,无为羞贱贫”(王褒《从军行二首》其二)等。总之,曹植的《白马篇》可以说奠定了曹魏以后游侠诗的基本风貌,其影响所及,通过后人纷起仿效而形成的系列歌诗作品亦可看出,如鲍照《代陈思王白马篇》、袁淑《效子建白马篇》,孔稚珪、沈约、王僧孺等人的《白马篇》等。
其次,通过对历史上真实游侠形象的讴歌来言志抒情,将游侠文化的现实性与艺术性有机结合了起来。张华《游侠篇》是最早直接以游侠为题的咏侠诗:
翩翩四公子,浊世称贤名。龙虎相交争,七国并抗衡。食客三千馀,门下多豪英。游说朝夕至,辩士自纵横。孟尝东出关,济身由鸡鸣。信陵西反魏,秦人不窥兵。赵胜南诅楚,乃与毛遂行。黄歇北适秦,太子还入荆。美哉游侠士,何以尚四卿。我则异於是,好古师老彭。
战国四公子作为权贵之侠,其结私交、养宾客,所成就的功业是远非一般游侠所能比拟的,其事迹在《汉书 游侠列传》中亦有所记录,“而赵相虞卿弃国捐君,以周穷交魏齐之厄;信陵无忌窃符矫命,戮将专师,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诸侯,显名天下,扼腕而游谈者,以四豪为称首。于是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诗人并没有站在班固的立场上看待战国四公子,而是肯定了他们的功业,虽然诗人宣称自己有与此完全不同的人生价值观。
南朝时期还出现了一系列以“刘生”为题的咏侠诗,如萧绎、徐陵、陈叔宝、江晖、张正见、柳庄、江总等人都有此类作品。《乐府诗集》卷二十四引《乐府解题》曰:“刘生不知何代人,齐梁已来为《刘生》辞者,皆称其任侠豪放,周游五陵三秦之地。或云抱剑专征,为符节官所未详也。”又引《古今乐录》曰:“梁鼓角横吹曲,有《东平刘生歌》,疑即此《刘生》也。”这里所说的《东平刘生歌》,只有“东平刘生安东子,树木稀,屋里无人看阿谁”这样几句。最早提到东平刘生的是收录在晋代《清商曲辞 西曲歌》中的《安东平》,诗的最后有“东平刘生,复感人情。与郎相知,当解千龄”之语。从这两首作品中看不出刘生的真实身份,很难将他与豪侠形象联系起来。刘生既不知为何代人,也没有留下真实姓名,或许主要来自于民间传说,但必定有一个现实原型存在。我们来看南朝诗人笔下的刘生:
任侠有刘生,然诺重西京。扶风好惊坐,长安恒借名。榴花聊夜饮,竹叶解朝酲。结交李都尉,遨游佳丽城。 (萧绎《刘生》)
游侠长安中,置驿过新丰。系钟蒲璧磬,鸣弦杨叶弓。孟公正惊客,朱家始卖僮。羞作荆卿笑,捧剑出辽东。 (陈叔宝《刘生》)
五陵多美选。六郡尽良家。刘生代豪荡。标举独荣华。宝剑长三尺。金樽满百花。唯当重意气。何处有骄奢。 (江晖《刘生》)
座惊称字孟,豪雄道姓刘。广陌通朱邸,大路起青楼。要贤驿已置,留宾辖且投。光斜日下雾,庭阴月上钩。 (柳庄《刘生》)(此诗引自《乐府诗集》卷24)